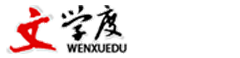第56章 类三通棋错一着
(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怎么了这是?”我瞧了瞧那双阿沅失手掉下的筷子又瞧了瞧她,终是什么都没有说……“小女无知,唐突了黄岛主,还请岛主宽恕!”武三通急急道歉,却也不见师父回,今儿这顿饭吃得委实是闹心了些,状况百出不说还着恼了师父。
“稚子胡闹罢了,家师又岂会真的计较?”大师兄悠悠一笑接过了话茬,也避免了大家再一次陷入尴尬,武三通朝着他微微点头抱以感激的笑,大师兄也跟着颔首示意,师父不动声色,当下一切看似平静和谐,我便也真个信了这眼前的妥帖安宁,却不想,到底是我欺人自欺了……
席间我们不再似往常那般说闹玩笑,以至于我突生觉想竟认为这用膳的时间比起往年还要来的漫长……
饭后回去时,陈师哥故意放慢了脚步等我,于是我便也小心配合着他的步伐,故作不知地陪着他继续走走停停,虽则内心里是无限的压抑,可那明面儿上却也到底是极和谐的……
只可惜好景不长,他忽的又驻了足,颇为沉重地看我道:“你不是不知么?”不知是他得了风寒还是怎的,那冷硬的声线竟是叫我觉得违和。
“什么?”我将思路转回与他的对话上,却发现自己并不能跟上他的节奏。
“同牢共食…你不是不知么?”他尴尬地笑笑,许是太久没有接触,我们都已生疏了往日那没心没肺的搭话方式……
“本来不知,后来又想起来了!”他问得生硬,我也答得含糊,好在他也并未追问,于是,两个都不懂得如何演戏的人相互迁就着小心翼翼地完成了一场并算不上出彩的表演……
“阿沅病好些了么?”沉默半晌之后,我终是再受不住那压抑的气氛遂牵起了话头。
“好多了,就是总不如往前,不过有武大哥日日为她施以针灸之术应也是不会再有什么大碍的,你便放心吧!”虽即不知他是在宽我心,还是阿沅当真已经大好,不过只消听他说的这般坦然,我便也放心了……
久久相默之后,我像是找出了什么症结似的,顷刻间变了脸色就问他:“不是说了半月就好,怎么却还在针灸呢?”
“阿沅身子素来孱弱,若不这般,往后怕是每月都要苦上一阵了!”他说这话时神色颇有些尴尬,约莫是怕我瞧出来才故作一本正经的焦虑状,我知他这般隐晦所指为何,只是仍然有些狐疑……
“那岂非是要武三通每月都在她水分来回间抚上一遭?”我反应过来,怒目圆睁地问罪于他,却听他说:“师妹,其实方才席间,你也见了武大哥与阿沅,他俩确实亲若父女,或许一切皆为你我臆测,何况当时阿沅沉珂病重,即便武大哥有何逾越举措也无非是关心则乱,你又何必如是抓着他不放咄咄相逼?”他蹙起剑眉,微有些无奈地将我望着,近来我最是瞧不惯的便是他这副模样,往前或还因自觉他为我牵动情绪而沾沾自喜,可现如今单是阿沅的儿女纠葛便已是叫我头痛了,更遑论是我自己?
“非是我抓着他不放,只是阿沅还小,需要后天引导,小孩子家家的不懂那些男女情爱,如果武大哥自己行为不端,就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何况阿沅少不更事情窦初开,若是……”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他冷不丁地出言打断于我,态度又是恶劣至此,我自也不会给他好脸子看,便冷声说:“我在说阿沅的事,你扯我做甚?”
“少不更事?情窦初开?看起来你很有感触啊,怎么,在你看来阿沅即将经历的都是你已经历过的了么?”大抵人年少时都易冲动,想的也多,若换了是后来,他怕是决不至于生出这些昏怪念头来的……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只怪当下,我也正年少,说起话来也颇盛气凌人,只见他闻言后一阵狂笑,笑了好一会儿才又止了声停下来咬牙切齿着向我道:“我胡说八道?你问问你自己,同牢共食,小师母,这些你敢说你从来都没想过么?”
“陈玄风!”两相争执不下,我便也逐渐没了气力,便干脆笑开道:“好,既然你今天非要把事扯到师父头上,我就跟你把话说开,莫说我是东邪的徒弟,就算不是,我也从不拘泥于那些小节,说句不好听的,武三通虽然为人粗糙,甚至连大字都识不得几个,可他对阿沅真心,虽然成不了什么大事,却也好歹不会坏事,若非他家中已有妻室,他和阿沅之间的事,我才懒得管!”
“你!”他闻言便是一愣,随即又怒目圆睁地瞪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见他这般我也颇觉解气,便故作盛气凌人地弯了嘴角嘲弄道:“如何?”话音刚落,他便已变了脸色,方才还因争吵而泛起潮红的面颊霎时惨白,他颓然地举起手指着我,随即又慢慢握成了拳头突地放下,我心下不安,也不欲他将我那玩笑气话给认真听了去,便想解释……
“我告诉你,你就是双重标准,若换了是师父,你还不定要……”我一下失言,待发觉时住口,却已是迟了,对面人被我这话儿一呛,片刻间也是说不出什么话来,偏偏又郁结在心,欲罢不能,便在半晌肿愣后又回过神来愀然道:“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师父,你就是不满我起先对师父言语不敬,你哪里是……”
“是!我就是!”我打断他,此刻竟是满心满眼地盼望着他不痛快,好似但凡是他心里不痛快了,我便能超生了一般,便尽捡些他不爱听的说……
“你…”他果真哑口无言,被我气得话都说不出了,可我知道,他本不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我怎样?我告诉你,我再怎么样也不过是跟你学的!”到底是我心有不甘,又或许终归是我入了障的缘故,偏执地急于想要证明些什么罢,我竟便就这般旁若无人地与他怄起了气来……
“若华,你就别要再同我赌气了,你若还生气,打我骂我都好,就是别要再说这样的话!” 他扳住我双肩,略带哀求地如是低声道。
想来我底气本就不足,与他那般长篇大论也无非是为形势所迫骑虎难下,如今他肯给我个台阶下,我确是意外,却也更是乐得自在。然,就在我眼见他分明气不顺却又从心来迎合于我时便不禁得来气,无奈我俩好容易才让那硝烟味给淡了下去,如今我确是再不肯让它继续浓了去,便也只得装作漫不经心地懒懒道:“便是见不得你这副低声下气的模样,师兄,你若想要女人服你,想我服你,你就得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你总以为我与师父有什么,事实却是没有,你总不肯信我,武三通于阿沅而言确非善类,结果却是……”我适当住口,果见他这回反应不似方才那般大了,只仍是有些抵触,微蹙了眉向我道:“我们不要再管武大哥的事了,就算你说的都对,可他的年龄阅历无不更盛我们一筹,他做事自有分寸,即使是他对阿沅当真存了心思也无非是想想聊作安慰罢了,我们又何必……”
“好容易才见着你们融洽起来了,怎么这会儿子功夫就又闹上了?闹什么呢?给人见着了也不嫌丢人?没得旁人又说我黄药师教不来徒弟!”清峻一言冷不防地由不远处传来,凌空而至,随后便听得另一道洪亮声线无奈奈地失笑道:“药兄,朝英没那意思!”
“我也没说是她,你这么紧张又是作甚?”说话间那三人便已是近了我与师哥身前。
“弟子知错,还请师父责罚。”果然,只有在这时候,我与我那师哥才是最有默契的,这会儿子我俩齐齐躬身,端的是惶恐萎靡,全然没了方才较劲儿时的力气,电光火石之间,只听得师父冷冷一笑道:“罚?若是罚你们有用,我早将你们……”
“黄岛主!若华年纪尚轻,不懂规矩也是在做难免,女儿家嘛,顽皮是顽皮了些,却也总不算过,慢慢驯教,会好的……”
“瞧你把你妹子说的,黄老邪说笑罢了,他的宝贝徒儿,这么一个玲珑剔透的小女娃娃,宠着纵着都来不及,又哪里舍得罚呢?”他们夫妇一唱一和地搭起了戏台子,何况林姐姐本意旨在为我求情,只是不知是否是世伯受林姐姐影响过重又或是当真人以群分,惘然间听了这么一句似乎是只有周伯通才说得出口的话还当真是有些惊诧,自初见,还不曾听重阳伯伯此般唤过师父……据曲师哥说,华山论剑之前,天下人便已尽知了师父东邪名号,武林中也有不少与师父同辈的惯唤他作“黄老邪”,倒是重阳伯伯一直药兄,黄岛主的唤,虽不算生分,却也不很亲切……也不知今儿个是怎么了,难不成太阳是打西边儿出来了么……我正摸不着头脑地如是臆测着,却又听师父闲闲道:我可没这本事去驯教她,嫂夫人既是挺身护短,不如就交由嫂夫人来驯教吧!
“我训教?黄岛主此话当真?”林姐姐闻言果真起心,兴致盎然地如是问道。谁知师父竟二话不说地抬眸正色道:“当真!”
我不满于他的一锤定音,便径自跪了下来肃然恭敬道:“我非牲畜非走兽,何来驯教?师父,若弟子犯错,您如何教训都好,弟子自当受罚……”
“是么?那玄风,你呢?”闻言他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眼中神色,仿佛厌恶又宛若感触,我自觉心虚与他对视便忙垂下了首,也总算他还记得有师兄这么一号人在身旁,只听师兄在一旁急急道:“弟子甘愿受罚,只求师父能饶过师妹此次……”
“你们当为师是豺狼还是虎豹?”他一下笑开,微带些挪揄地如是问道。
“师父……”我惊讶于他的反应,一时间竟也答不上话来。
“方才还争执不休的,如今却是同仇敌忾了?想是你们都拿我当了对头吧!”他有意无意地转动着手中玉箫,那是前年,大师兄特特从冰岛寻来的青玉锻制而成的上品,大约这世间是再觅不到第二把了……想起师父先前在我面前碎箫的场景,我便是不禁地牙齿打颤,到底小儿心性,不愿他又随便气了去,便又抿了唇战战兢兢地道:“弟子不敢。”
“我很可怕?”他这回倒不笑了,只是摆正了脸色,一副师威赫赫的模样,末了又挑了眉去看我那已然无话的师兄道:“玄风,你说。”
”弟子……弟子……不敢……”
“药兄!算了罢,竖子无心之言罢了!”重阳伯伯适时地出言打了围场,却见师父蓦地皱眉,一句“还不快滚回去?尽在人前给我丢人现眼!”轰然乍现,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我俩耳边,此刻我们那儿还记得方才嫌隙,只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便赶忙告退了。
俗话说的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那日我平白地被师父说了一通,可经此一役,师兄却是再不拿那些恼人的风月事来烦我了……
想来也是,连日来我苛尽本分,力求平稳,再不似往常那般闹腾,就连师父见了我这儿股子真诚劲儿也确实动了磨砺我性子的心思,便叫了我每日午时过后去他房里陪他对弈,也不知是前世遗梦,还是今生迷蒙,冥冥中我总好似是听谁常在我耳畔低回浅吟:人生便如棋局,若下棋时耐心,则局尾时开心;若下棋时倾心,则局尾时放心;一子错虽也不至满盘皆落索,却到底是添了些瓶颈和阻碍的……
春来寒去却往往最难将息,前人的风骨摆在这儿生机萌发的和风里固然是不适宜却也到底是有几分道理,可不,那三尺棱冰虽是渐趋消融了,可阿沅的病情却是无常反复总不见好,一日我在师父房里与他对弈时听他讲说由是武三通指力有限的缘故,这才叫阿沅白捱了那么许久苦痛,偏偏林姐姐服食还笼期间最是动不得元气是以也无法替阿沅根除那月事阻塞之苦,他说这话时声轻若浮,情绪上也并没有什么起伏,想来他本也不是医者,自然也没有那医者特有的病患父母之心;他也不是什么丹士大儒,不会兼怀天下视生命为浮屠;他更不是那武三通之流的粗浅庸夫,想必阿蘅之前也未有对哪个十四五的姑娘生过些什么惜玉怜花的心境。
“你也别要这副哀怨死相对着我,该出手时为师自会出手。”我回过神时他正眼皮都不抬一下地兀自专注着棋局,忽的又拈了一粒黑子来,只听得啪嗒一声,那冷暖玉棋子便已干脆落在了那经由整块琉璃砌就而成的棋盘上。
“真的?”我早已没了计较棋路胜负的心思只一心揣度于他这话的真假。
“你真道我会见死不救?”他睨我一眼,跟着扳起了脸来颇带些冷峻地如是说道。
说起来师父那翻脸比翻书还快的绝技我也算是幼承庭训早就习惯了,是以这些年来我偶尔也渐渐不再惧于他那冷戾师威,先前那般遭际也可说是家常便饭,索性有我那贼汉子作陪,被罚时也不外如是,我们也权当了是顽儿,苦中作乐罢了。不过自当下而言,此情此景,即使我心中当真这般想他却也还是终究不敢外露在颜色之中的,当下得了他为阿沅诊治的承诺才是最为紧要的,我如是想着便不自觉地带了娇意向他谄媚道:“师父怎么这样想?徒儿是当真无计可施了这才……”
我有意停顿,故作为难状,随后果见他哂笑着开口戏谑道:“怎么,黔驴技穷了?”
“是,徒儿的确一筹莫展。”我说这话时低眉恭敬,只因我当真没把握于阿沅病情……
“本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你也未免太有些小题大做了。”他低头继续端详着那棋局,语调平平地如是说道。闻言我多少有些些恼,便甩了手中棋子道:“徒儿给师父扫兴了,那师父便跟自己弈棋吧!徒儿告退。”我撑着案几起身,正想着往外去,却不想他突然扣住我那还留在桌案上的手波澜不惊地低声问道:“我准你走了么?”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桎梏和他向来不形于色的薄怒,我微有些慌乱地与他对望了好一阵,少顷才又问他:“师父还有何吩咐么?”
他又加重了些力道却并不答话,我睁大了眼睛看他,正迷惘于他纠结的眉头里那复杂的情绪究竟出自于何时却又见他松了手,双眉也是舒展着的样子,面色如常的,好似并没有什么纷乱心事,恍然方才那一切,皆是我自己个儿魂入了遭太虚之境似的……
“不论你心里如何看待武三通,他终究是你段世伯一手调教的入室弟子,何况来者是客,往后别再要我看到你对他如前日那般态度!”
“是,弟子遵命!”我俯身恭敬行下一礼,他仍自端坐在那儿,黔首冥思着他的棋局,不一会儿竟当真与自己博弈了起来,这是他一个人的局,由他设由他立,自然也由他一人左右延续,我在时他或可陪着我拆上几招聊作消遣,若我不在……他怕便是连多念我一下都嫌费神了吧……
小时候总听娘亲说,薄唇之人大多寡情,师父呢?他也是薄情之人么?不,他对蓉儿与阿蘅不就很好么?而且,他对弟子也不是说不好,就是有时脾性古怪了些,我们又都怕他,是以谁也不会有那个胆去找他促膝长谈,于是这些年里我们就越发不懂师父心中所想了,大抵那些深藏不露的世外高人们都是如此的吧,他们总有自己的世界,而往往那些另他们沉醉其中不可自拔的秘境又都不是我这样的普通人所能理解看透的……
“在想什么?你如此这般站着做甚?莫非你还想练折腰舞不成?站累了就坐下罢!”他终于抬头,双眼里却像是覆上了层疲惫的样子。
“武三通其人,粗是粗糙了些,待你那何姑娘却是不差的,就算是你卖她一个面子也罢,好歹也是系出大理段氏的弟子,你何苦又如此视他如洪水猛兽?”他闭上眼,抬起手揉了揉额角,良久才又睁开眼如是说道。
“师父认为武大哥对阿沅很好?”我问,却听他兴致勃勃地反问:“你倒是说说,他待何姑娘哪儿不好了?”
“没有,很好!好的很!”当下我正暗自鄙弃着武三通对阿沅那过分的好,便就全不知了自个儿此刻狰狞着的面目咬牙切齿地是有多违和……
“你如是厌弃于他究竟是何故?可是有何误会?来给师父说说,教师父也……”他话至此处便陡然没了声息,旋即似是想起了些什么极骇人的噩魇便又紧锁了双眉来看我。
我也不知是怎么了,只瞧着他那如同被蜜蜂蜇了一般的表情便觉气闷,谁知他弹指间又换了神情起身笑道:“不过是教你些待客之道罢了,还起了脾性了!也罢,瞧不上便瞧不上吧,你段世叔座下有渔农工书四大弟子,为师素来最瞧不上的,也便是那畏首畏尾的村夫武三通!”
“吼!师父自个儿不待见的人却偏要我待见,这是甚么理?”我一屁股坐下来,大快朵颐地撑着头凶巴巴地望着他,却见他不着痕迹地道:“你到底与他同辈,何况你们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若不喜欢他,离他远儿点就是了,何至于要像现在这般与他明面儿上过不去?”
“师父何时也学得旁人那般虚伪了?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难不成还要徒儿对着自个儿不喜欢的人强装欣然强掩恶寒么?”我收起那幅吊儿郎当的样子正色道,突然一下间晃神,又飘渺着思绪自顾自地喃喃道:“是了,师父一向也便是如此的,便是喜欢也强说作不喜欢,便是讨厌也强说作不讨厌的!”
“放肆!”我乍然回神,他面上顷刻间便已像是覆上了一层霜,神情冷冷地将我打量着,玉碎般的声音恁地流泄而出,叫我一时忘了害怕,忘了畏惧,于是便只知驻足,为他停留在了这原地……
俄而,我终是从那凄迷的恍惚之中堕突出来,我这儿正斟酌着思量到底该如何开口,师父却仍自斜坐在哪儿,正以手叩击着他的“兵士”,那有一下没一下的敲屐之声随即清脆,却又掺了些许疏离的冷漠,叫我一时惶恐不得言语,于是,又过食顷,直至我再忍受不住那违和的静默,才到底屈从了他淫威,瑟瑟开口道:“徒儿失言……”
大约是他本也未想真与我这儿小孩儿一般见识抑或是他念我年幼且又能及时悔过悬崖勒马便也并未真个动气,只抬了眼道:“外头阳光正好,你若觉得耽在我这儿无事做,便自去找乐子吧!”
得他此话我便如获大释一般逃也似的走了……
出得门外来到了清音洞边的一处小池塘时我才察觉出,师父果真没有骗我,隆冬以来,日头还从未如今天这般好过,大好时光放在眼前我不珍惜又是为的哪般?难道往后都要这般下去么?
岁月静好,抚着晨露在那缦回盘囷的檐角上打着转儿,一会儿又顺势滴入这塘里,圈起点点磷光,我斜倚着那阑干坐下,拨弄着尚未成型的芰荷,任由那温润的阳光爬上我的眼角撒野……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往日瞧你纤腰窄臂的,还道你定无那杜诗里的慵懒风韵,如今不想却是为师错了……”师父含着笑向我走来,眼光好似是在看我,又好似是在看我身后的那丛芰荷,眼里仿佛有我,又仿佛没有我……他最近老是这般让人摸不着情绪,前一刻还顶真着要治罪于你这会儿子却又好言好语地俨然一副和蔼的良善之人样子……
其实和师父相处久了便会知道,他绝非是那良善之辈……若他当真起了心思要叫你不痛快,那你的命便如同是那附在骨肉里的蛆一般,挖不得取不去,只能连着那皮肉一起,慢慢地,腐臭,溃烂……这才是真正的,求生不得,求死无门……我如是想着,当下我只道自己已对师父那狠辣手段有所了解,又怎知,原不过是凤毛麟角,若言狠辣,谁比得上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不过是我当下有关于江湖血腥的懵懂套词罢了……
“师父!”当下他笑地如沐春风,全没有方才的慑人气势,眉眼弯弯地似是想起了些什么不为人知的芳情绮思,然我却仍念着那跗骨之刑的悚栗……
“折腾够了便回罢!外头风大,若是再染了寒气就不好了!”他近了我身,为我弹去了那不知何时落在了我发上的雪花……
“下雪了?”我惊道,却听他哈哈一笑说:“是你运道好!”
我伸了手出来去接那扬扬洒洒的雪花,依稀记得,我与他初遇之时,也正是这大雪纷飞的季节,便有感而发地叹道:“真快啊!”
“什么真快?”他挑了眉来看我,我却不看他,只盯着那手中落雪顾左右而言他道:“人都说雪水比起雨水是来得格外纯净的,徒儿记得,师父好似是嗜酒的吧?”
“不知用这雪水来酿桃花春是种什么光景呢?想必滋味不会比阿茴那坛差到哪儿去……”我一下转头去看他,却见他不置可否地摊了双手道:“你若酿,我便喝,甘醇与否,于我不过一线,并无分别……”听他这般说,我也顿觉自己好生无趣,便慢吞吞地起了身向他行了礼道:“徒儿告退。”
后来再见师父是在元宵前夕,我仍旧在他房里,与他下棋对弈,正月里我那贼师兄将阿沅的病情都细细与师父说了个全,师父也答允请诊,如此一来,也算是解决了我一大桩烦恼,如今竟是连棋路都觉得愈走愈顺。
也对,人一旦没了包袱顾忌,为学做事便也多了份冲劲儿,其间纵然或者多经波折,却也总是能事半功倍绝处逢生的。
“你欧阳伯伯前些日子派人来送了庚帖,我与你重阳伯伯已商量了应下,到时带你一起,去他那白驼山看看!”他下完一子,忽的停顿,轻描淡写地如是说道。
“欧阳伯伯?白驼山?”我眯起眼睛看他,却听他又说:“恩,也算是个风光秀丽的宝地了,你不是要看雪么?这几月白驼山下雪不止,等你到了那儿,定又是个奇观。”
“大雪封山,我们如何进得去?”我绞着手将视线由他身上又转回了棋盘上。
“这有何难?你也未免太小瞧为师了!”他笑,笑地倨傲,我听出他话里的孤高自恃便也不再多言,只漫不经心地道:“那可得带上阿沅,她好容易才痊愈,是应该外出去走走了……”
“恩。何姑娘与你一向说得来,若她也去,岂不是正好便宜了你?”他一面下子一面温温地如是说道。
“那倒也是,怕只怕,有人心系爱女,不肯答应……”我笑,微有些促狭却刻薄地如是说道。
“那恐怕是要让你失望,前些天我着武三通替何姑娘去寻那开经解淤的药引子,他三天三夜未眠往返了冀州一遭带回了培母芍,如今寒邪侵体正躺在病榻之上,怕是管不了你那阿沅如今是何作为了……”
“什么?什么培母芍?我如何不知?”我一下失了分寸,提高了声量问他,却听他云淡风轻地道:“是我吩咐,不准他们告诉你。”
“师父!”我气急地嚷他,却听他不紧不慢地问:“告诉你了又能怎样?你能往返冀州,只用三日?”
“三天三夜往返冀州?这怎么可能?”我吃吓,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却听他叹道:“你实不该怀疑你武大哥用心……浮世间,怕再没人能为何姑娘做到这般了……”
“是……徒儿错了,武大哥对阿沅便如同师父对我一般,是真个好的……”我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简直语出惊人,想是当下只惦着某人竟为了女儿将那冀州距离临安的遥遥千里当作了是三天三夜的短足游程一般的事,便也不禁动容……
他闻言也是一阵默然,片刻后回了神,匆匆落下一子,却不想竟被我给钻了空子,无奈起手亡回,他便也只得失笑着叹了句:“罢了!大势已去……不错,几日不曾见你,棋术却还算有进益!”
“是师父分心才是!”大抵是他往日里甚少夸我的缘故,我竟便因了他这一句夸奖而洋洋得意了起来,这人啊,总是不得而益奋起,一旦太过满意太过得意便也就容易忘了形……
想来我虽跋扈虽傲物,可那该有的自省我却还是有的,方才那句已算得上是作乱犯上了,既然师父大肚,不与我计较,我自更该要懂得进退,谨言慎行才是……
“你既知为师分心,那你自个儿也定是分了心的!”他失笑地看着我如是道,我有意将话题引开去,便追根究底地问他:“是的,只是,往日里徒儿走子,师父总也是老早就察觉了的,那么与其说是徒儿一贯心有旁鹜,不如说师父你也一向是同样有旁鹜的,怎么今日……”
“你想问我,何以你今日会赢么?”他抬眸,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进而解释道:“不错,往日里为师与你弈棋,多半也非是真正专心,只是今日,仓促间应下你几位世叔的庚贴,难免有些烦乱。”
“哦,我大概懂了,事失利,往往而用心躁也?可是,师父应了便应了,哪里还需要想那么许多呢?假使师父方才当真不愿,那直接推了便是,师父一句话的事儿,总也不会是甚么难题吧!”我琢磨着他这话的真假不怀好意地如是问道。
“好了好了!不过是方才错了心思输了你一着,哪里来的这么许多问题?”他摆摆手板起了脸来如是道。
“因为师父这下得要应我一件事呀!”我笑,笑得娇俏,或许还生出了些许媚意来……
“鬼灵精的丫头!你倒是说说,为师何时又允诺过你什么了呢?”他也笑,笑地春风化雨。
闻言我也不答话,他见我踌躇不言语便又径自改了口道:“好罢,你且说说,要我应你什么?”
“徒儿不敢求师父其他,只求……只求师父能高抬贵手,躬身替徒儿在这儿桃花岛中扎下一个秋千……”我低头浅笑着如是说道。说完复又抬头去看他,双眼中盈盈所勾勒的,尽是派小女儿的旖旎风情……
他闻言也不恼,只静静瞧了我一会儿,许久才轻笑着说:“这有什么难办?你若喜欢,为师便帮你在这儿,扎一个秋千!”
“谢谢师父!”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如果您中途有事离开,请按CTRL+D键保存当前页面至收藏夹,以便以后接着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