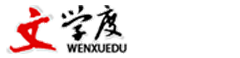正文 锋芒毕露
(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竖日朝堂,皇帝下旨斥责两个四品大臣,教子不善,为虎作伥,直把两人说得是老脸通红,砰砰磕头告罪,遂,念其悔过,罚奉半年,破天站在文官队列垂目冷笑,这两人放任外戚作恶,却只罚奉半年,根本不伤点毫,皇帝又当庭赞誉破天为官清正,恪尽职守,赏了好些银两,破天跪地谢恩,那些个被自己上过折子的大臣纷纷投以眼刃,丞相更是脸色不善,皇帝这般举措,本就是将破天推到了风暴中心,只怕群臣记恨,自己一个不小心便被抓住痛脚。不过,还是有好处,起码已有不少满腔热血的才子递了帖子想要拜入门下,不过破天明着还是推却了,暗着自然是好生接待,要知道,她可是想在朝中扶植一股新势力,好扎稳根基瞅准时机推七皇子出来。
皇帝发作大臣后,又吩咐礼部、工部着手开始准备今年的秋猎,还有不到半月时日,大到随行名单,小到吃穿衣物,皆要好生备着,破天昨儿个已看过先帝在朝时期的行猎与奉天条例,赶忙走出队列,匍匐在地,进言道:“皇上,历来行猎十岁已上皇子皆在随行之列,秋猎乃要事,若随行无皇子,岂不是叫朝阳笑话我奉天后继无人?微臣斗胆,请皇上准二皇子,五皇子,七皇子,十皇子随驾。”
殿内安静得紧,只余破天方才的余音回旋,低眉顺目,看着澄澄发亮的青玉地面,挺着背任皇帝目光灼灼搁浅于身,你喜欢盯,随你盯,反正她又不会少一块肉,而且,她这御史可是专管这有违法例之事,皇子随行乃天经地义,至于皇帝愿不愿意,与她何干?她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问题。
洵亲王瞧着这阵势不对,皇上自登位后随行人选从未有过一个皇子,如今被破天撂了面子,只怕心中盛怒,急忙走出队列,附和道:“皇上,御史所言甚是,若不遣皇子随行,只怕让朝阳看低,以为我奉天无人啊。”破天在暗地丢了个感激的眼神给洵亲王,这老王爷明里暗里帮衬多次,倒是个明理的。
皇帝面露不愉,也不发话,眸子转到丞相身上,那意思摆明就是要丞相出来和破天唱唱对台戏,丞相在心头苦笑一声,走出队列道:“皇上,几位皇子骑射尚且未学几年,恐不精,微臣只怕届时出岔子,这事可晚几年再议,来年秋猎再带众皇子随行也不是不可。”
破天眉头轻皱,立马反驳道:“丞相此言差矣,我奉天皇子自幼能武能文,就算如丞相所说骑射不精,能出去增长见识,取长补短,看清自个儿的不足也是好的,祖制有约,奉天皇子十岁后便有遂吾皇出行的条文,而今,二皇子已抵十六岁,还未出宫建府,也未随驾出行,这不是有违祖制吗?”
安王闻得破天此话,是虚汗直冒,要知道,这皇子出宫建府就代表着要入朝为官,这皇帝就是怕皇子甚早入朝拉帮结党,危及皇位,才将二皇子圈于宫中,群臣谁人不知?今儿个他这女儿竟挑破了这层纸,安王吞了口唾沫,飞快瞧了眼高台上的皇帝,果不其然,皇帝面已显怒,双眼瞪大老大,若非破天这御史身份专管这等违背祖制之事,只怕早就唤近卫军将人拖出去宰了。
丞相也是没有料到,这尚破天有如此魄力,竟然敢当面说出此等话,简直就是在群臣面前打了皇帝的颜面,双腿一软,差点没站稳,破天倒是不慌,一副忠心耿耿满腔热血的表情,直直盯着皇帝,那是半点台阶也不给皇帝留。
“这事,朕倒是未详加考虑,”皇帝心中憋屈,一口闷气卡在胸膛,怒极反笑,是字字咬牙吞泪,看着破天的目光越发狠厉,眸底杀机片片,“如此,着礼部将二皇子、五皇子、七皇子、十皇子加入随行名单,秋猎之时,朕要好生考校皇儿的骑射,扬我奉天国威。”
“扬我奉天国威。”
“扬我奉天国威。”
…………
下方群臣叩首高呼,破天端着皇帝深明大义的模样跟着叩拜,那架势,只差没把这皇帝生生气晕过去,强扯出笑,挥袍下朝,破天起身,自然得到洵亲王等老臣的夸赞,话里话外透着她乃忠烈,一心为奉天着想的味道,听得破天一阵胃疼,不过,想起方才皇帝脸上憋屈的表情,倒也欢喜,凤眼含笑,与群臣寒暄,一时好不热闹。
该,谁叫你封我做御史?这不是存心找不爽么?
皇帝下朝后直奔御书房,步子冲冲,脸色极其不好,进了书房,径直将案上折子全数挥洒落地,怒火未消,抱起矮几上的青花瓷盏,哗啦一声砸了个粉碎,守在御书房外的近卫军是心提到嗓子眼,就怕一个不小心被皇上迁怒,发作一通后,这御书房里是杂乱无章,那些个花瓶、茶杯、器皿散落一地,皇帝气喘吁吁瘫在软塌上,眸子冷得骇人,方泰缩在一边,不敢出声。
且不管皇帝是如何生气,破天下朝后便被自家阿玛提着衣领拽回了安王府,府内下人翘首盯着,那目光亮得很,破天面儿上丢脸,踉跄着步子,求饶道:“阿玛,快松开,丢脸死了。”
安王不管不顾,管家一看这架势不好,赶忙去卧房找舒云求救,话儿说得不清不楚,直让舒云以为破天犯了什么大事,这安王是要弑女,踩着高脚后跟瓶口鞋,哒哒跑到书房,还未进前院,就被侍卫拦下。
“王妃请回,王爷说了,没有吩咐谁都不准进去。”
“放肆,本王妃也是你们能拦的?”舒云气得脸颊通红,奈何这俩侍卫是纹丝不动,任她如何如何踢踹也不肯放行,“你……你们……”
“王妃莫要难为奴才。”侍卫也苦逼啊,一边儿是王爷一边儿是王妃,他们做下人的哪个都得罪不起,舒云指着拦路侍卫,手指颤个不停,这会儿她就怕天儿被安王怎么了,踮起脚朝里头高喊:“王爷——王爷——”
没有人应答,这俩个侍卫没了办法,对视一眼,左边个低声对着舒云恭敬说道:“王妃莫唤,公主没事的,待到王爷怒气消了自然出来了。”
这话说得,舒云寻思一会儿,迟疑道:“你敢作保证,本王妃的天儿无事?”
“奴才用脑袋担保公主没事。”闻言,舒云这才将安心不少,又盯着书房紧闭的大门半天,才一步一回头出了前院,两个侍卫苦笑,这叫什么事?
书房内,安王端坐木椅上,跟前还放着温茶,搁着点心,耳鬓发丝隐白,面上几道细长皱纹却丝毫未减俊容,书架挨着墙排成排,破天板着脸正跪在冰凉瓦砖上,双手高过头,举着一把封鞘长剑,这还是她头一次被阿玛体罚,心头憋着气,也不讨饶,晌午已过,父女俩愣是没出过房门,一个坐着一个跪着,没人吭声,脾气一样倔。
破天自持未做错什么,朝堂之上她虽为难皇帝,却字字有理,奈何阿玛不管不顾竟当着那么多下人的面对自己是又提又骂,她如何不怒?如何不委屈?凤眼沉沉无光,低垂着头盯着反射阳光灿灿的瓦砖,黑发高束,只余两戳垂在肩头,薄唇隐有齿印,眉目却带固执,四肢僵硬,手中长剑乃安王佩剑,玄铁所造,削铁如泥,重量惊人,堪堪举了一个多时辰,竟已麻了双臂,奈何,一口气憋在胸前,始终不肯开口认错。
安王虽气破天在众人前撂了皇帝颜面,却更怕,怕有朝一日自个儿实权全无,破天这性子势必要被皇帝责难,铁了心想要制破天,可眼看着这爱女宁愿受罪也不肯低头,心还是痛的,坐在木椅上长叹口气,眸子略带倦色,道:“天儿,阿玛如今是管不了你了。”
破天身体一颤,咬唇道:“阿玛。”
“你性子这般刚烈,若是男儿固然是好,可奈何你是女儿身,如今虽在朝堂却露锋芒,若阿玛老了,如何护你周全?皇上不过是隐忍不发,若当真要办你,亦是容易,你再这般鲁莽,只怕徒惹灾祸啊。”
闻言,破天心头感动,亦知晓阿玛是为她好,双手一软,长剑竟哐当一声落了地,垂头不语,她确实是被皇帝今儿早朝将她推到风尖浪口的举措气到,也想着借由这次秋猎将七皇子引入众人眼中,可换个方向想,那皇帝当真如此好摆布?自个儿将七皇子交给太后,已是让皇上猜忌,此番动作,只怕更让皇帝忌惮,稍有不慎只怕给阿玛惹个结党营私的名头,岂不是亲手递上把柄给皇帝抓?心头一寒,已知这次过于急迫,未收敛锋芒。
书房一片安静,只闻屋外几声鸟鸣,安王瞧着破天半响不语,面露颓色,心知必是被自个儿触到痛处,心下一软,起身走到破天身边,伸手拽住手臂,将破天强行拖起,破寒为笑,揉着破天的脑袋瓜子温和言道:“你莫要怪阿玛小题大做,此番皇上不追究,不过是被你抓了先,没有驳斥的缘由,你心是好的,可做法却过了,若换个法子,也许既能达成目的,又能免去灾祸,日后做事多想想,柔能克刚,智能胜武。”
柔能克刚,破天默念着阿玛说的词儿,闭眼冥神,半响,凤眼睁开,黑眸有流光划过,神采奕奕,好生惑人,薄唇轻抿划开弧度,眉眼皆笑,撩袍半退,弯下腰,道:“女儿谢阿玛提点。”
“好,知错能改,这才是本王的女儿!”厚实手掌拍打在背上,不痛却意外地暖人心肺,英眉弯成两道,父女俩并肩站于房内,偶有畅笑顺门缝划出院落,舒云一席曳地粉色长衫立于前院外,枝头泛绿,院内花朵簇簇,姹紫嫣红悄然盛开多多硕壮,日光洋洋洒洒,晃人眼帘。
当晚,破天着素白锦袍带莫飞行于花街柳巷,花楼烟客聚集,莺莺燕燕欢声笑语,偶有怜儿抚琴清唱,偶有客房断续娇喘,行至后院,山石林间悠然自得,刘旭仍煮了壶好茶款待,破天撩袍落座,捧起玉白茶盏放至鼻下,芝兰之气扑鼻,怡人心肺,破天笑言:“每每喝刘兄的茶便觉是极为享受之事,若非知你,我定强行绑回府,叫你做那煮茶人。”
刘旭摇头轻笑,按着茶壶盖子将水注满茶盏,热气腾腾升空,晃得那双眸子仿若雾中,“公主这话可是说不得,御史大人怎能做那掳人行径?平白辱没了这清廉名头。”
“你倒是专以讽我为乐。”破天不怒,将茶盖掀开一半,送入嘴中,顿觉齿颊留香,正想夸赞几句,却见茶壶热水溅出几滴于刘旭手背,这人眉头一皱轻声冷嘶,破天极为自然唤了个小厮,取来药膏亲手涂在刘旭手背之上,软膏凉凉入骨,带点晶莹,刘旭亦是取了方帕子为破天拭手,此举虽暧昧,却也无关风月。
“我今儿个来,可是专门讨你要一份这五皇子的资报,你可莫要狮子大开口又是一千两。”破天笑言,浑然不觉方才与刘旭的动作过于暧昧,这人约莫就缺了那根情筋,刘旭已习惯她这般,双手捧着热乎乎的茶盏,眯眼道:“好,这次分文不取,赶明就把东西送到御史府,公主可满意?”
“自然。”她二人没那些个礼仪限制,两只白玉茶盏轻碰,擒笑交目。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如果您中途有事离开,请按CTRL+D键保存当前页面至收藏夹,以便以后接着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