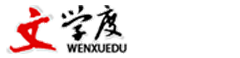正文 剪不断理还乱(一)
(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阴雨连连,顺飞檐滴落,似晶莹串珠,落座于僻静地儿的宅院,高挂御史匾,匾上篆字笔走龙蛇,两尊栩栩石狮嘴含偌大石珠,红木柱子端立门前两方,有小厮瞧着一身朝服正盈盈走来的破天,忙打千行礼,伸手放下门栓,恭迎破天出府。【吱——】庄严肃穆的大门缓缓打开,破天执着一柄鹅黄油伞,踏黑色马靴,刚撩袍跨出门沿,便见台阶左侧,廊檐下的角落有一卷曲人影,弓着身包裹成团,瑟瑟发抖。
“主子。”小厮随着破天的目光移去,自是见着了那人,低声唤着。
“他一宿未离?”
“是,奴才劝过了,可这人固执得很,说是无论如何也要再见主子一面。”小厮恭敬答话,就恐哪处惹了破天,半弯着腰只低头瞧着地。
“倒是个忠心的奴才。”破天叹了声,侧耳吩咐小厮去往丞相府将此事告知丞相,她从来都不是心慈手软的人,既已决定了断,便不可能再藕断丝连。
天色阴沉得紧,乌云遮幕,寒风扑哧吹动,时辰尚早街上少有行人,路面雨水兮兮,破天吩咐完后,便举步上了府外软轿,马靴踩在小坑之上,溅起坑中雨水涟漪,染湿了脚尖。
“起轿吧。”浮动的暗色帘子后传出淡淡的声音,轿夫打了个寒颤,抬着软轿疾行,不多会儿后方大宅便成了黑影,若隐若现。
破天甚少为已决定的事儿后悔,待到软轿行于午门,已然将双儿之事抛诸脑后,挑帘下了轿,禁宫把守的近卫军纷纷行礼,于午门处瞭望远处飞檐走兽宏伟庄重的大殿,只觉心中有些乏,说不清究竟为何,挥手叫了起,正欲进宫,便闻后方有轿子徐徐行来,鹅黄小轿慢悠悠行于午门,轿帘绣着八爪盘曲金龙,破天轻笑,将手中油伞撑开,便上前嚷道,“阿玛今儿来得真早。”
“天儿。”安王快步下轿,破天将油伞往安王那处移了少许,冰凉雨水瞬间染湿身上轻裘,半身露于伞外,盘着的青丝挂着细细密密的砂糖,有小太监递来油伞,安王顺手接过,父女俩一边儿说着闲话儿,一边儿穿过层层宫墙往朝殿行去。
“快入十二月了,又过一年,岁月不饶人啊。”安王亲手打着伞,瞅着左右雨幕中的树海花团,眉目染了少许沧桑,青石小道淌着细细潺水,淅淅沥沥,雨帘漫漫,倒是给这深宫添了几分雅致。
破天听着安王这番有感而发的话儿,心头一凉,亦是同感,年关后便是大选,而后又是科举,一年一年反复,抬眸盯着安王发白的鬓发,心下微酸,又恐说错话害阿玛伤感,便转了话题,凤眼微眯,指着身侧树海中一团傲然红梅枝桠,道,“可不是,红梅朵朵,开得好生艳,每每晨起入朝路禁此道,便能闻扑鼻梅香,若哪日在王府后院种上几株,一家子团坐烧酒,可不热闹?”
“这主意倒是可行。”安王阖眼一想,连声赞着,只在脑中稍一想娇妻爱女随侧,畅快言笑,便觉热潮滚滚抚上心头,倒是冲淡了方才的愁死,破天一路说着这些个话儿,逗得安王好生开怀,绵绵细雨中,父女相视笑着说着,待到踏上百步云梯,立于大殿红廊下,才敛了嘴边笑容,将油伞递给伺候太监,双双进了殿。
今日早朝,丞相姗姗来迟,皇帝不渝,问及缘由,丞相老泪纵横称幼子风寒入体,身体抱恙未愈,自己心力交瘁告罪圣上,皇帝不忍,如何肯罚?头一回在群臣面前柔和了声,安抚丞相,倒让破天心头冷嘶,这皇帝当真宠信君家一脉,要知道上朝来迟,说大了可是不敬之罪,便是杖责亦无可厚非,而皇帝却只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甚至下旨再遣太医院几个医术甚好的太医朝后往丞相府诊治,如此隆恩,就不知大臣们如何猜度了。
洵亲王等老臣垂目不语,安王等武将亦闭口不言,只文官一脉面露喜色,六部几个尚书侍郎,脸泛愁色,想来定是心中有所打算,破天不慌,凤眼于暗处悄然与后排几个年轻官员对视,似安抚,转瞬便移开。
而后,兵部尚书上折,称边防四城过冬置的兵备短缺,其中棉袍铠甲尤其缺乏,上请皇帝拨粮饷以便军士日夜操练之需,此话得安王等武将附议,皇帝不语,遂问及众人意见,丞相率先迈步,伏地朗道,“启禀皇上,如今天下安定,我奉天国富民强,微臣以为应调户部查四城军营中无户之人,先解甲安置令其回归故土,再查持兵户户口人数,再行拨下饷银。”
“丞相此言不妥。”安王皱眉,跨步与丞相并肩分庭对视,一个擒笑,一个肃容,一个文弱,一个强壮,论气势,丞相自不比安王,奈何多年朝堂滚爬亦是极具心机,只端着笑,抱拳问道,“不知本相所说有何不妥?”
皇帝面色一沉,亦跟着询问,“安王且说说看,待朕定夺。”
“皇上,数多年前战役险胜,劳民伤财,如今虽天下安定,但不可就此懈怠,朝阳虎视眈眈,两国虽签订和平条约,但也不可不防,若遣无兵户的士兵解甲归田,岂不乱了军心?如今军中大多乃苦命百姓,未在兵户记录,若只为了粮饷,便遣士兵回乡,倘若有何变数,岂不乱了根基?”安王说得是句句在理,发自肺腑,不少武将亦走出附和,文官一脉也有不少人昂首驳斥,两派人头一回不顾身份吵得不可开交,破天连连皱眉,奈何她只是一三品御史,断没有插手此等事的理由,只能埋首站于原地。
“够了,吵吵闹闹成何体统?”皇帝冷下脸,揉着眉心大声斥道,众人歇语伏地请罪,偌大殿中安静得只余呼吸声,皇帝瞅了几眼丞相,又看了几眼安王,心中合计后继续道,“户部尚书。”
“臣在。”
“朕命你于七日内交四城军营中有兵户的人数清理后呈上,至于兵部上奏之事,容后再议。”皇帝这话摆明了是同意丞相的进言,安王张口欲唤,却被皇帝挥袍制止,一众武将面上阵阵青白,一派文官却昂首挺胸,退朝后,安王的脸色是黑得彻底,丞相笑得开怀,拍着安王的肩头,道,“安王爷,方才本相有所得罪,还望王爷莫要放在心上,你我二人都是为皇上做事,想来王爷肚子能乘船,定不会将这等小事放在心上。”
“丞相说得甚是,甚是。”安王硬是挤出笑,尴尬得很,又与丞相谈了两句,才分道各自离去,几个武将面上愤愤,出了大殿于云梯上朝安王进言说道,“王爷,皇上此番调整大军只怕……”
“莫要多言。”安王不欲再听,忙呵斥,眼睛在四下扫了一圈,待到群臣尽数离去,才对着方才开口的武将道,“圣上已下旨,此事不可逆转,你等多说亦无益,小心祸从口出。”
那武将听言后,再多的不平亦只能往肚子里放,朝安王行礼便离了去,破天安静站在阿玛身侧,瞧着庄严殿宇高耸云下,只觉渗人,索性插在四城军中的破天骑早早便被她安了户,伤不到分毫,只是阿玛上折被驳,恐怕心中郁闷,遂陪着安王回府后,又好生宽慰,安王心中不忿,连午膳亦未用便进了书房,舒云无法,只能遣破天前去瞧,因着王府三个主子皆不爽,府内下人更是安分,就怕祸及自身。
破天先遣伙房做了阿玛甚喜的几样小菜,又备了薄酒,亲手端着托盘行于书房外,抬手叩响房门,安王开门后见来人是破天,亦侧身放人入内,父女俩围坐于小塌矮几边,破天执酒宽慰,又捡了好些趣事,才堪堪将安王安抚好,皇帝此番动作当真是在众人面前抬了丞相一脉,贬了武将一行,生生打了安王一个没脸,破天心头也是气,但此刻她亦是无可奈何,只是心中对权势的渴望愈发大了起来。
这天下,只有位极人臣,高于朝堂,立于顶端,才能保能护能安身边的人。
时辰不早,连绵小雨停了,只地面仍淌着潺水,寒风瑟瑟吹动青丝,拂在脸上甚是挠人,破天在王府用过晚膳,便辞了父母回了大宅,于书房内提笔疾书,白纸黑字仔细巡检后才绑于信鸽腿上,撑在四方窗柩边,瞧着灰白鸽子扇着翅膀腾飞天际,半响,才揉着脸换了一身朝服,着月牙白的长衫,系银白貂裘,一席黑发披肩,凤眼灼灼,一身出尘风姿如若谪仙,领着莫飞出了府。
“主子欲往哪方去?”莫飞仍旧带着常年不变的人皮面具,与破天隔着小半步的距离,小心护着主子于热闹的人群中,破天轻笑,手中转着一柄合拢的折扇,“天色沉沉,良辰美景下,自然是要寻一怜儿作陪,你家主子我正要寻花问柳去。”
这话,说得是理所当然,素来温和的面上甚至挂了几分邪魅的笑,朝街上一不识的官家小姐抛去秋波,引得那小姐面红耳赤,莫飞连连皱眉,不知主子这油腔滑调究竟是向谁学来,明明是闺中女子,竟比那翩翩儿郎还要出彩,凤眼秋波暗送,勾人魂魄。
花街仍旧灯火通明,扮得花枝招展的怜儿正于二楼舞动丝巾,对着下方路人笑得人比花娇,杂闹繁华,人声鼎沸,火红灯笼从街头挂到街尾,人影沸沸来来往往甚是热闹,破天一副贵公子扮相,貌比潘安,自然是引得数多楼中老鸨缠身,胭脂水粉酒色酒香弥漫空中,莫飞掩住口鼻,身上寒气四散,破天一路不知拒绝了多少个怜儿的拉扯,明明是冬日,额上却硬是出了密汗,在这明晃光线下,衬得脸颊更是晶莹透彻。
“哎哟,这不是天少吗?快进来快进来。”花楼龟奴于门前瞧见破天,是笑灿了脸,忙弯腰作揖,好生热情,破天轻笑,捻了腰间锦袋摸出碎银放在龟奴掌心,手腕折扇在空中划了一圈,轻扣在其脑门,倜傥道,“行了,本公子熟门熟路还不知你这番行做究竟是何意?”
龟奴得了赏,欢喜得紧,嘿嘿笑着,引了破天进楼,楼中大厅仍是一片糜烂,好几个陪侍的怜儿身上单薄衣衫退到了胸口,玉胸挺挺,沟壑成线撩人心动,欢声笑语绕梁,破天又不是头回见着这样的场景,自然不觉不妥,正行过大厅长梯,要往后院儿去,岂料被梯上喝得神志不清的男子拽住了身上轻裘,英眉微蹙,侧目道,“放手!”
“哟,这是打哪儿来的男怜,真真是貌美如花,瞧这双眼,勾得小爷春心荡漾,就想就地解决一番。”男子面色红通,醉意朦胧,左手还提着一酒壶,开口便能闻到满嘴的酒气,破天不怒反笑,手中折扇猛地拍开这人拽着自己衣衫的手背,朝后退了两步,正想发怒,老鸨恐事情闹大,忙上前安抚,遣了个美貌娇娘伺候嚷嚷连连的男子上二楼客房,又亲自向破天行礼道歉,破天也懒得计较,不看僧面看佛面,若非不得已,她倒是不会当众给刘旭的人一个没脸。
“罢了,老鸨这张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我若再斤斤计较,岂不成了小人?你且去忙你的,我自个儿寻刘旭去。”盈盈浅笑,老鸨见破天大量,自然欢喜,乐呵着下去,破天举步悠悠晃过一条长廊,行至后院,许是楼中大厅太暖,刚一踏进院子,便觉寒气铺面,微微打了个颤,莫飞仍留于原处,静看破天行入山石后。
参天大树绿叶染黄,洋洋洒洒于空中落了地儿,青石小道积了好些雨水,暮色四合,空镶弯月,冷清月光倾洒,倒影于水坑之中,远离了前边儿热闹的纸醉金迷,自然闲适,破天还未行至竹椅边儿上,便见刘旭一席素白长衫,腿盖一截软毡,正低眉摆弄着竹桌上的茶具,手边儿隔着一暖炉,热气腾腾。
“啧啧,还没走进就闻到一股茶香扑鼻而来,这前有怜儿闹堂,后有清茶度日,你这小日子过得好生让人羡慕。”破天温和笑着,步子不紧不慢缓缓走到竹椅上,压了压轻裘边角落座,刘旭不答,只拿起茶壶给破天满了一盅,伸手递过,才幽幽道,“公主且尝尝。”
“呵,你泡的茶怎会差?”破天接过,先闻茶香,才掀开茶盖于袅袅雾气中轻抿,“好茶。”
刘旭摇头笑开,给自己满了一盅,捧着茶盏,二人于竹椅上半倚对坐,望着无垠天际,只闻热水于炉上沸沸之声,偶有几声鸟鸣,偶有几缕清风,端得是悠闲,半响,刘旭半阖着眼,才问起破天来意,“今日怎有闲情来我这儿?”
“瞧你说的,不过是琐事烦心,四下走走,顺便来你这儿讨杯好茶。”破天一手捧着紫砂茶盏,一手盖着额头,脖颈微扬靠着清凉竹椅,青丝于身侧扑散开来,面容淡淡。
刘旭心知破天为何烦心,也不劝,低声道,“若你烦,我差楼里琴姬为你弹上一曲,如何?”
“你倒真当我是那寻花问柳的人?”破天伸手将茶盏往矮几上一搁,侧身正对刘旭,黑眸若这天,望不到底,亦瞧不真切,刘旭垂眸,食指顺着茶盏缓慢划着,“听说昨日丞相府二公子抱恙,公主拒不相见?”
这话题转得,破天眉头一皱,心下好笑,颔首应了声,刘旭转了眸子瞧着园中山石,又道,“如此清秀公子,清莲于世,不染污秽,公主怎忍得下心。”
“打什么哑谜,我心中所想你又怎会不知?不过是迟早的事。”刘旭喜与她抬杠,嘴仗打过不少,破天不欲在这事儿上多谈,端起茶盏一仰而尽,下意识摸出宽袖中的锦帕想要拭唇,刚展开,便愣了,刘旭抬眼瞅着破天难得的愣神,疑惑道,“怎么?锦帕可有不妥?”
“没,”捻着锦帕的指头一紧,生生在这帕子上掐了道印子,也没用,匆忙收回袖中,二人自是又说起旁的话题,约莫谈了半个时辰,破天才起身告辞,刘旭也不拦,只等破天朝前走了几步后,才低头盯着盏中茶水,喃了句,“朝阳王爷此时正在楼中。”
闻言,破天步子一顿,有些恼怒,却又不知这情绪究竟为何,凤眼泛冷,一席出尘白衣如雪,落拓且笔直的脊梁峥峥如竹,负手于背后,侧身扫了眼正埋首玩着茶盏的刘旭,“腿在他身上,与我何干?你又何须说与我听?”言罢,口中冷哼一声,撩袍而去,步子甚快,踩得青石地面哒哒的响,刘旭目送破天离开,手中茶水已凉透,闭目靠于竹椅上,长叹。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如果您中途有事离开,请按CTRL+D键保存当前页面至收藏夹,以便以后接着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