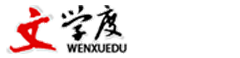正文 年后杂事
(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新年余热未散,独孤月称久留数日,于宫中拜别,皇帝本想摆宴相送,却被其推拒,只遣了群臣于深宫殿宇前迎送朝阳使臣,独孤月一骑戎马傲然于云梯下,抱拳道:“陛下不必多送,此番两国能明文通商已解了本王之忧,若有机会,本王定再来贵国。”皇帝温和笑道:“甚是甚是,独孤王爷下次来奉天,朕定厚待。”
独孤月大手一挥,随行侍卫随即翻身上马,动作利落,眸子暗暗扫过女眷前列的破天,见到其云髻之上插着的木簪子,心头自是欢喜,面上的笑倒是多了几分真实,唇瓣蠕动,而后,便挥动马鞭,转身携使臣离去。
大红衣衫合着骏马,马蹄哒哒,那人似踏云而来,短暂滞留又踏云归去,于百步云梯之上远观其越行越远的背影,破天一时也说不清心中的情绪为何,只那人方才的唇语于心尖荡漾,他说今日她很美,淡淡一句赞誉,便胜过数多,拨动一池春水。
“天儿,天儿。”耳际闻得额娘几声轻唤,忙收拾了心中杂乱的思绪,抬眸望去。
“你怎这般失神?”舒云轻拽着破天的手腕,下巴朝四周微扬,破天一瞧,方才迎送的队列已缓缓散开,心中暗骂了独孤月几句,便挂着笑,陪着额娘下了云梯,自是没有瞧见文官队列,眉头紧皱的君念奴,与皇帝身旁眸子死寂的尚雅至,真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大年刚过,群臣自是备礼互相走动,因着朝中文武两派素来不合,而破天这御史又太过刚正,前来拜年的朝臣自是少得可怜,比起丞相府的门庭若市,她这儿倒多了几分冷清,彩儿正端着青铜暖炉放到破天身旁的矮几上,一张小嘴嘟得都快挂壶,破天将手中书卷摊在一边,托着下巴问道:“尚棋,你可知是谁招惹了彩儿?这大清早的,怎就一副委屈的样子?”
正安静站在一旁的尚棋闻得话儿,忙娇笑回道:“奴婢也不知呢。”
“主子!!”彩儿跺着脚,一脸愤愤,破天连忙罢手,将暖炉揽入双手之中,挑眉又问:“怎了?”
“奴婢这不是为主子抱不平。”
“我有什么不平要你这丫头来抱?”破天深感好笑,连连摇头晃脑,尚棋亦觉她二人甚逗,忙捻着衣袖遮住弯起的嘴角。
“哼,主子是没瞧见,方才我出府购置些礼物,便见那相府是人来人往,可我们这儿却连人影都没一个,主子怎就不担心?”
“哦?”破天惊疑一声,低眉不语,若她这御史宅拜年的人多了,只怕第一个不允的便是皇帝,她手下的那些门生自是想备礼登门拜年,却被她在暗处叮嘱不可如此,才消了念头,如今这冷清,虽叫外人笑话,却能安那九五之尊的心,只是这些话她断不会说与彩儿听,面上便摆了副虚心受教的模样,任这丫头怒斥那些个朝臣。
约莫半柱香的时间,这口若悬河的丫头才停了话,破天赶忙伸手递了杯茶过去,凤眼弯弯,“说累了?喝口茶歇歇嘴再继续。”
“主子!”彩儿又急又怒,她在这儿愤愤不平半天,可这正主却觉无关痛痒,如何不气?双颊是憋得胀红,若非碍于身份,只怕是要甩破天脸色看的。
“好了,腿长在人家身上,说再多有什么用?这样不是很好,还能省下几杯茶。”她倒是真不在意,有些东西摆在明上是要掉脑袋的事儿,隐忍不发才是王道。
一月大选过后,破天旧话重提,上奏天听,称二五两位皇子已到出府年龄不可久居深宫,皇帝允,赐下府邸,赐婚二人,二皇子乃皇后嫡子,身份自是尊贵,婚配吏部尚书之女,大婚后,入吏部,五皇子无权无势,皇帝愧疚,赐婚九门提督之女,入户部,两道赐婚旨意一下,礼部是忙得天昏地暗,每每入朝便瞧见礼部尚书与礼部侍郎脸上的黑眼圈。
三月后的文武大考,全国才子齐聚帝都,试题由皇帝亲出,翰林院学士与丞相监考,阅卷乃几个皇帝亲信文官,破天这御史只每日在坊间游荡,下达民生,坊间书屋自是借机印刷了数本书册,什么《科考试题》,什么《考题卷宗》数不胜数,有投机取巧之辈,想寻路子探得今年科举试题,奈何今年风声甚是紧张,无人敢顶风作案,倒是让一帮贪官如吞黄连,苦水直冒。
与独孤月同谋行商一事已被破天记在心上,差人给刘旭送了封信,要得奉天做大的几个商贾名讳与详细资料,既然决定做,便放手去做,她从来都不是拖泥带水之人,刘旭当晚便来了答复,称主营丝绸的商贾乃卫城的卫家,旗下店铺广布整个奉天,上个家主年纪老迈,已在日前退位让其子卫夫管事,这卫夫年纪虽轻,却通透,十岁之时便接手卫城商铺,管理有条不紊未得丝毫差错,乃商人之资,破天得到答复后,忙写信函一封命莫飞送于卫夫,若其有意,便邀于帝都一聚。
这事儿,她自然是私下办的,未曾告知旁人,就恐走漏风声,时至三月下旬,旭阳高挂,垂柳长青,院中花团簇簇,争奇斗艳,雏鸟于林间鸣叫,山水石间,万物逢春迎绿,白日风中带香,今儿早朝下得甚早,破天着了一身朝服还未换下,刚乘软轿回了府邸,还未行进正厅,便见府中下人小跑过来,步子略显急促,便滞了步子,探身问道:“怎的这般匆忙?”
“主子,方才驿馆来人送了封信,说是主子好友送至。”下人忙伸手从怀中掏出一封被印泥封好的黄呈密信,递给破天,低眉一瞧,信封上只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写着:公主亲启。
破天颔首将信放进袖中,挥手让其下去,心中已知晓是谁,只是暗叹这独孤月胆大,竟在这青天白日差驿馆的人送来,转念又觉,倒是附和这人的性子,吩咐彩儿不必随旁伺候,便行进书房,从袖口拿出信,搁在桌案上,也不着急打开,踱步于窗柩,将大开的窗户关好,这才慢悠悠展信来看
厚厚三页信纸,多已调情暧昧的词段为主,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什么两情若是长久时岂在朝朝夕夕,直把破天看得又气又笑,寥寥扫了几眼,废话连篇,这正事儿却只短短几句,大意是破天若要行商,只需飞鸽传书于他,便可供给丝绸,交货后再付银两,破天将信纸来回又看了一遍,只觉额上青筋跳个不停,你说这独孤月是抽的哪门子疯?三页信纸,正事却只这么一句,枉费她还以为是有什么大事,尖锐的指甲深深刺透信纸,怒极反笑,打开抽屉将这信展平好生放好,又摊过一旁的干净信札,攥了墨,提笔疾书,写道:
【见信如见人,可见王爷腹中空空,满腹废话】
写好后,正欲唤莫飞将信送到驿站,转瞬又忆起这莫飞早被她遣去了卫城哪里还在府中?心下一叹,又瞥见桌上墨迹未干的信笺,屈指轻叩桌沿,抚额不语,待到心中情绪回复平静,才将纸揉成一团丢到地上,她又不是不知这独孤月的性子,怎就与他置气了?实在与她往日的行事相左,索性亦懒得再回,从书架抽出几本杂书,便在这书房内细细看了起来。
此时,深宫之中,因着二五两位皇子迁居府邸,还未达出府岁数的其他皇子自是各居皇子所,一人一座屋子,白日入书房听夫子教学,晌午便回各自院子用膳,趁着今日阳光甚好,尚雅至遣了太监于御花园中摘了几株娇艳欲滴的花儿搁入青花瓷瓶,吩咐太监往太后与淑妃两处送去,称得孝心,又打赏了好些银子给这太监,自是叫其感激,忙称定办好此事,尚雅至应了声,便移步回了小院儿,还未行进屋子,便见院外五皇子的贴身太监正于树下踱步。
“你这是在做什么?”瞧见尚雅至回来,太监忙挥手打千,低头答话:“回七爷,五爷寻你好一会儿了,此时正在屋内久候。”
尚雅至凝了凝眉,绕过太监,便进了屋子,如今这五皇子已出宫建府,自是甚少于宫中走动,如今冒然前来,也不知为何,他与这宫中众皇子素来不亲近,除了上次与这五哥有过帝都一日游,便未曾独处,实在摸不透其来意,行到屋前,便见五皇子正坐于四方仙桌边转着茶盏品茶,一身朝服还未换下。
“五皇子。”
尚雅竹闻得尚雅至的声音,忙侧身,虚扶了一把,清秀的面容端出一抹亲近的笑,“怎如此生分?唤我一句五哥便是。”
尚雅至不语,落座于木椅之上,双手合拳搁在膝盖上头,低眉顺目,尚雅竹瞧见这人如此淡漠,也不气,负手起身,于房内踱步,约莫来回走了两圈,才低声道:“七弟这屋子好生简单,还有一股药味,可是身子又不好了?”
尚雅至摇头,二人一个说一个听,一个问一个不答,纵使是再好的脾气也被这木头磨出了火,尚雅竹探出脑袋在屋外看了看,合上门,又关了窗子,屋内静谧,只余二人的呼吸,一个绵长一个急促,尚雅至侧身抬眸,一双黑中带蓝的眸子幽幽,死灰一片,“你想做什么?”
“七弟,今儿你可得给我个话,东宫之位你可想要?”尚雅竹压低了声音凑到尚雅至耳边沉声问道,这声音虽低,却如惊雷在尚雅至平静的心水炸响,身子一僵,掌心立有指甲深陷,头微垂着不答话,可这反映却已让尚雅竹探了个底,心下一松,忙伸手掀过茶盏,半响又言:“你若有此心,皇兄定助你一臂之力。”
尚雅至抬眸与尚雅竹对望,一个坚定如磐石一个平静如深海,上身往旁边移了少许,才吐了话:“为什么?”
“只有你登位,五哥才能有达成夙愿的那一天。”他的愿望很小,只是想远离朝堂远离皇室,奈何投错了胎,如今二皇子进得朝堂,行事孤傲,对他这无权无势的皇子自是瞧不上眼,若其登位日子定难过,膝下群弟又年幼,只有这七皇子可扶植,那天出游,他便是瞧出七弟与世凰公主相交甚好,若得安王一脉拥立,又有他从旁协助,登帝位,定不难,皇室中人,押宝只一次,若对了,便双赢,若错了,便是挫骨扬灰的下场,如今他便赌这一赌。
尚雅至探身压着素白袖口给自个儿满了杯茶,临空举起,二人对碰,似立下誓约,达成同盟。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如果您中途有事离开,请按CTRL+D键保存当前页面至收藏夹,以便以后接着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