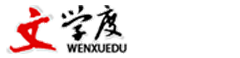第九章 第九章(34)北郑行(七)
(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在金喜的指引下,霍士其他们很快就到了一大片宅院前。这里原来是北郑县的官驿,十八年被突竭茨人放火烧过一回,后来由州府拨了点钱粮重建的。因为当时北郑才历过兵祸,地方上招不到民伕,没办法就把事情委托给驻军,所以驿馆的无论是门楼还是庭院都没有美观可谈,完全就是按囤兵军寨的标准修建,讲求的就是简单粗犷结实耐用。院墙也垒得高砌得厚,外面搭人梯都未必能摸到砖帽,紧急情况下在墙内叠几张桌椅,弓手就能上墙头阻敌。驿馆里彻底就是兵营的模样,什么庑廊回廊角门照壁的无关摆设一样不见,就是一条石板路通向一箭地外一个三房四舍的单进小院落;石板道旁边左右各二整齐地接出四个更小的院落。
如今右军指挥衙门就设在北郑城里,因此这里住的全是进城办事的官兵,人多眼杂,又是傍晚吃夜饭前后,四个小院子门口蹲着站着的都是兵,即便段四已经让人把马匹都牵去前街的边军指挥所暂留,一多半的人也留在驿馆外,可前面走着两个七品校尉,后面还有一个被人架着胳膊的七品校尉,前后十来个人走在道路中间,马刺磕在石板上喀哩喀啦乱响,想不多看几眼都不可能。转眼间连院子里的人听到动静也跑了出来看希奇,借着院门上的灯笼火把光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地相互打听。其中也有人认识金喜,跑上来和他招呼说话,眼睛却把段四和霍士其上下乱瞄。
驿丞也听说来了几个大官,带个差役急慌慌地从后面撵上来。他也认识金喜,瞅一眼段四和霍士其还有那些护卫,没和他们见礼就先哭丧个脸说:“金指挥,你一下领来这么多人,驿馆里可是住不下了啊。”
这时候从前边小院里又出来一个八品校尉,大跨步地走过来,疑惑地扫视众人一眼,行个军礼说道:“禀三位大人,右军的几位旅帅眼下正在那个院子商谈机要,要是三位大人没有军务,那就请留步。”说完就立在道路中间,目光微微低垂却不让开。
段四瞥了金喜一眼,看金喜稍稍摇头表示不认识,明白这不是姬正的兵。招了下手示意那个校尉走近两步,从怀里掏出霍士其的将军关防,不动声色地问道:“认识这个不?”小校皱起眉头使劲辨认了一下,神色突然一凝,退后一步就要重新行礼,立刻便被段四用眼神制止住。
段四收起将军关防,问道,“里面是哪几位旅帅?”
小校犹豫了一下。
段四也不催他。眼见想静悄悄和姬正见面的事情已经不可能,他心头马上就拿定主意,头稍微一摆,轻轻一句“布置关防”,留在驿馆门外的二十多号人立刻就呼呼啦啦地进来,二话不说就把两边看热闹的人朝旁边的小院子里赶。一开始还有人骂骂咧咧地诅咒喝骂,随即就被这些人的勋衔职务吓了一跳。二十多个人里面八九品的校尉占了一小半,一个个怀里掏出来的全是睚眦吞口的燕山提督府铜铁腰牌,有个模样长得很象突竭茨人的军官甚至掏出了银腰牌一一天爷,这里还有个七品校尉!
一眨眼工夫驿馆里就清净下来。所有不相干的人连带驿丞杂役全部都被赶进屋里,人人心头打鼓样乱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在院子里负责警戒的提督府护卫只是禁止大家喧哗走动,其余的并不理会,慌乱了一阵也就各自安心下来,一头轮流趴着门缝朝外张望,一头纷纷议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过来询问的小校已经彻底傻眼了。段四连说两遍“带路”,他才噢噢连声地急忙转身,脚下迈着步,眼神却在乱瞟。金喜在旁边好心提醒他:“兄弟,机灵点,别让大家都不痛快。”
那处院落里的人也被外面的纷乱惊动了,又有人站出来查问。段四看都不看门口的两三个警卫一眼,也不理会什么“止步”、“停下”的喝令,大踏步踏上了台阶,迈过门槛拿眼睛把院子里一扫,目光就落在正屋滴水檐下站着的三个青袍人身上。
“是谁他娘的吃撑了来这里搅事?是老金么?”又有个人挑门帘从屋里出来,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没穿袍子就披一件大褂,手里还端着个碗,望了一眼段四身后的金喜,很不耐烦地喝问,“你和谁在一起?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想搞什么名堂?要是惊动了指挥衙门那群疯狗,你就别想消停了!我告诉你,粮饷的事回头我去帮你说情,你千万不要在这时候闹事,不然神仙都救……”话音到此便戛然而止。说话的人到现在才看清楚院子里的情形。一群如狼似虎的兵正在鱼贯而入,随即就散开,院里不停响起低声呵斥命令卫兵缴械进屋的声音,偶尔一两个人敢反抗立刻就被几刀背砸翻,随即就听见有人猛地惊呓一声喊道:“弟兄们谁都不要乱动!他们是提督府大将军身边的护卫!”
这声叱喊划过,院子里的人个个都象中了鬼怪传说神仙传记里的定身法一样,泥塑木雕般全都傻呆呆地楞住了。
伴随着“不许喧哗不许走动擅动者斩”的低沉喝令,顷刻之间院子里原本有的十几个人就剩下正屋前被七八个护卫围起来的四个旅帅。
段四哈哈一笑走下石阶,马鞭子拍打着手掌,笑道:“我能搞个屁的名堂啊。就是这几天闲得心慌,就想找你喝上几口。”两步走上前很随便地抬手行个礼,又说,“钱旅帅,范旅帅,好久不见,我可是想你们想得要死了。一一这两位有点面生,想来也是右军哪个旅的旅帅副旅吧?”指了身边的金喜说道,“他是谁,你们都认识,我就不费唾沫绍介了。我是提督府副尉四。”说着把身子一让,两个兵把霍士其搀扶过来。“这一位你们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不过就算不认识至少也应该听说过一一这位就是燕山提督府印剑都检事、游击将军霍士其。”
钱老三范全还有两个旅帅急忙间根本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全都哈着嘴一脸呆滞地望着他,直到听说了那一长串的勋衔职务再加“霍士其”仨字,才猛地反应过来。钱老三和范全连礼都顾不上行,一左一右先把霍士其接过来,一面小心翼翼地扶着,一面嘴里乌嘈嘈地乱喊乱骂:
“屠贤,赶紧抱几床棉被出来铺座椅里!”
“段四!你搞的什么撮鬼名堂?把十七叔作弄成这样,你他娘地不想活了!”
段四立在阶前口下令道:“吩咐一声,门口小心在意。从现在起,驿站里只许进不许出,有妄动的又或是敢聒噪的,不问缘由,通通剁了扔后面喂狗。”
“是!”两个军官答应一声,就急忙跑出去传令布置。
段四这才满脸假笑对另外两个旅帅说道:“两位大人也请吧。外面风大,小心着凉。”说着也不管人家情愿不情愿,一边挽了一条胳膊,半是硬请半是活拽地就把两个还没醒过神的校尉拉进屋。
这是三间上房里最大的正屋。和驿站的整体风格一致,这里同样是不求美观只讲实用,就算屋角摆着两张大木床和两个盔甲架子,剩下的地方也能再宽宽绰绰地摆两三桌八人的席面。大木床枕头被褥棉絮衣裳裹得乱七八糟,盔甲架上除了盔甲还挂着几只雉鸡和一条不知道什么野兽牲畜的风干腿子肉。两张木床之间靠墙,堆了两层平常人家炮制酱菜用的大土陶坛子,有的坛子还用泥封着油纸,有的就纯是空罐罐。西壁靠墙放着一个烛山,七八只羊油大蜡火光熊熊,照得屋里一片通明。屋子正中的一张大木桌上大半边都是狼籍的杯盘,碗叠碗盘摞盘,筷子、酒盅、鸡鸭骨头丢得到处都是;一个大木盘里还扔着两根啃得就剩几丝肉的棒子骨……
霍士其坐在桌后的主位上。他面前的桌子一角已经收拾出来,眼下商成的钧令和他的将军关防就并排摆在那里。段四面无表情地端立在他背后。范全、姬正、钱老三,还有右军甲旅旅帅马琛、右军乙旅旅帅秦淦和金喜,分坐在方桌两边。屋子里还有个范全的部下屠贤屏息静气地立在屋子一角。他低着头,佝偻着腰,人几乎贴在墙上,似乎想拼命地把自己填塞进烛火映照不到的阴影里。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开口说话了。
自从段四简明扼要地介绍完中军及左军一部在莫干的情况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说话。
段四说的一切实在是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大将军竟然打到了莫干?大将军不仅占领了莫干,还把莫干的敌人连同黑水城和阿勒古的援军全部撵到了黑水河西岸,还在白狼山里堵住了东庐谷王?因为右军擅自违背军令,中路军最终不得不放弃已经取得的优势战局,不得不在强敌环视的不利情况下开始撤退?大将军亲自断后?鹿河老营还不知道能不能守住……
这些简直教人不敢想象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从段四嘴里跳出来。一下子面对如此众多的惊人消息,在座的右路军将领谁都无法说话。也没有人还说得出话。段四说的和他们从右军衙门听来的军报完全不一样!不是说大将军在打到鹿河就开始撤退了么?不是说东庐谷王集合大军尾随追击么?不是说留镇方向可能需要右军增援么?不是说……
他们的判断力和思路已经彻底混乱了。他们需要时间去判断段四说的到底是真还是假,需要时间去判断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更需要时间去让自己恢复一个将领应有的判断能力!
屋里非常安静。安静得每个人都能清楚听到自己的沉重的喘息声和急促的心跳声。令人无比压抑的寂静中,蜡芯燃烧时爆出的每一声碎响,完全就和雷雨天撕破天空的霹雳一样响亮。实在是**静了。人们甚至能听到桌边其他人吞咽唾沫喉头关节蠕动的声音……
好象是过了很长时间,但是每个人都觉得似乎只是过了那么一刹那,霍士其吃力地从座椅里坐直了身,抬起一条虚弱的胳膊,捏起商成给自己的钧令:“你们都看过这条命令了吧?”
几位旅帅都默默点头。
“这份钧令不是我伪造的吧?”
所有人依旧是表情木然地点头,异口同声地说:“不是!”
在这些人当中,姬正和霍士其的私交甚笃,他的嘴角牵扯着想开句玩笑,谁知道才张开嘴还没来得及吐出一个字,就被霍士其冰冷的阴沉目光给逼得咽了回去。他一口气没换过来,立刻吭哧吭哧地咳嗽起来,而且越咳越是厉害。最后咳得他完全撑不起腰,直接就趴在面前的一盆肉汤里。就算这样,他都还在吭哧吭哧地咳嗽。看来,他前几天从马上摔下来,不仅折断了两跟肋骨,也许还伤到了肺……
但是没有人理会他。几个旅帅都把腰板挺得笔直,双手叠膝,昂着头,目光定定地注视着前方。只要看看段四进门之后的一连串举动,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霍士其来北郑绝对不是钧令上说的什么劳什子“公干”!和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相比较,咳嗽又不会死人……
霍士其也在咳。但是不是姬正的那种连续不断地咳,而是隔半天轻轻地咳一下。他的咳声浅得似乎只是从喉咙处发出来的,假如不注意的话,也许就会被人忽略过去;可又似乎空洞得让人觉得他的身体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大窟窿,而且还是那种深不见底的大裂缝,黑黝黝的的,完全看不到一些的光亮……
霍士其喘息了几声,喉咙里滚动着粘稠的痰音,又说道:“你们怎么想的?”
所有人都知道这话是指什么。每个人的心头都是蓦地一紧。但是没有一个人的目光有所动摇,依旧定定地直视着前方。更没有回答这个看起来很难回答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范全,”
“职下在!”范全低叱一声象根木头桩子一样跳起来立正。
“你是怎么想的?”
“一切听霍将军将令!”
霍士其点了点头,摆手让他坐下。
“钱老三,你呢?”
“一切遵霍将军将令!”
“姬正,”
“职下,职下……没的说。霍将军怎么说,职……职下就怎么做。”姬正边咳边说道。
看霍士其望想自己,右军甲旅旅帅马琛没等他发问,自己就站起来,恭敬说道:“右军甲旅上下,一切遵从督帅钧令和霍将军将令!”
霍士其耷拉下眼眉,轻笑了一声,说:“督帅的钧令就是让我到北郑和右军中公干。”他把商成的钧令重新放到桌上,收敛起笑容说道,“督帅还说,只要李慎肯出兵,无论什么样的条件,都让我答应他。段副尉,督帅当时是不是这样说的?”段四道:“是。这是督帅的原话。前天下午,在莫干寨里,督帅就是这样说的。”霍士其点了点头,吁了口气,继续说道,“不过哩,我现在不打算执行督帅的钧令。那么马校尉,在我不打算执行督帅钧令的情况下,你会遵从我的将令么?”
马琛的脸色一下就变得苍白起来。他完全没有想到霍士其会这样说。他更没有设想过这种情形下自己应该说什么。他绷紧了面孔努力挺直了腰,接连吞了好几口唾沫,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偷偷地打量了一下钱老三和范全他们。可让他失望的,这些人似乎都没听到霍士其刚才说了些什么,还是那付木雕泥塑般的冷漠表情。他还想从霍士其的脸上寻找到一个可能的答案。然而经过六七天连续不断奔波的霍士其,脸上糊着厚厚的一层油泥和灰尘,这就象个泥脸壳,把他脸上的所有表情都隐藏起来。
霍士其耷拉下眼睑,目光垂下来,停留到桌子上的一碟盐酱上。他似乎忽然对这碟子酱感到非常有兴趣。
马琛痛苦地思虑了半天,最终还是艰难地做出了选择:“职下,惟霍将军马首是瞻……”
霍士其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既没点头首肯马琛的决定,也没有出言鼓励这位右军甲旅的旅帅。他的目光缓缓地但是很坚决地移到右军乙旅旅帅秦淦身上。他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平静的眼神,冷冷地观察着这位李慎的头号心腹大将。
秦淦没有望向霍士其。他很平静地说道:“李慎将军是燕山中军司马,是端州指挥,他有权决定右军的进退和端州方向的军事行动。这一点,想来督帅和霍将军都很清楚。”
“是,他的确有这个权利。但是我想追究的不是这个事情。我只想追究他凭什么擅自封锁端州与燕州方向的交通,他为什么要向督帅封锁右军撤退的消息。秦校尉想必知道,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吧。”
秦淦一下就沉默了。良久,他才慢慢说道:“霍将军也知道,本朝立国一百多年,以前还从来没有提督擅杀方面大将的事情。督帅……”
“以前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霍士其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打断了他的话。桌上的碗盏盘碟叮叮当当一阵乱跳。“你说是督帅擅杀方面大员?我告诉你:他,李慎!就凭他李慎!一一他还不配污了督帅的刀!他不配!”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迸出这句话,口水都喷到秦淦的脸上。“他李慎是个什么东西,还想让和尚背个‘擅杀’的罪名?他是个什么东西?除了骄横跋扈,除了夺别人功劳,除了欺蒙谎骗,除了朝腰里塞银钱,他还能做什么?你说,你说他李慎除了会干这些,他还会干什么?”他把桌子拍得噼噼啪啪乱响,两颊红潮得就象绕着两团炭火,眼睛里喷出吃人的火焰,满屋子都是他愤怒的咆哮!
“他李慎是个东西?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走一地落一地的骂一一我就没听谁替他说一句好话!远了不扯,就说这北郑县城!他是端州指挥,他怎么指挥北郑的?就把北郑指挥出这付模样?三个月换两个县令,他就是这样指挥的?别人宁可坐在家里居闲,也没人愿意来北郑!为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秦淦不说话了。霍士其说的这些话,提的这些问,他每一个都能回答上来,但是没一个答案能让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出来。
“我今天和你秦淦明白地说了!我就和你们明白地说,我,霍士其,燕山屹县霍士其,今天晚上就要处置了李慎!”他通红着俩眼,就象一头狂怒之中的老虎,恶狠狠地把目光从范全身上一路扫视到秦淦。“谁他娘的敢阻挡我,”他一拳头擂在桌子上,轰然一声响中他冷森森说道,“那我就先处置了他!”
……当晚子时初,燕山右军司马李慎,因为谎报军情、擅自撤退、构陷友军及临敌失机等六项罪名,在北郑右军指挥临时衙门里被燕山提督府印剑都检事霍士其下令当场处死。燕山右军司马督尉谢旦,以胁谋共犯、知机不报等七罪,当场处死。其余处死者计一十二人,羁押四十七人,禁行止二十六人。
霍士其随即以燕山提督府印剑都检事身份下令,暂由端州右军乙旅旅帅秦淦为首、右军旅帅马琛、钱老三、范全为辅,四个共同筹谋决断端州方向防御,并派出四个骑旅,分由马直川和古唐驿道,迅疾进军草原,解救鹿河老营。
做完这些安排,霍士其摘将军盔,解将军甲,除佩剑,散发髻,褐衣短裳,自请束缚,命燕山提督府副尉段四解送自己去燕州。
在去燕州的路上,段四曾经很不理解地问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段四觉得,即便是为了商成,霍士其也不用这样做的……
这个问题把霍士其难住了。他是为了和尚么?当然,这是为了和尚。但是,他心里很明白,他这样做并不全是为了和尚。事实上,他这样做,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和尚。更多的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他本来就该这样做吧。谁让他是个燕山人呢?不!这样说也不对!可他实在是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自己的想法……
他坐在狭窄的囚笼里,手脚都戴着桎梏,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
生平第一次,他开始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探寻起自己在思想上的变化……
七天后,鹿河之战结束,得到增援的燕山中军在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之后,在右军四个骑旅的掩护下缓缓后退。五月初六,草原上的最后一支赵军走过火烧台,退回留镇……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如果您中途有事离开,请按CTRL+D键保存当前页面至收藏夹,以便以后接着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