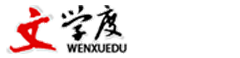正文 卷五 卑微者的血红眼睛
(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天暖起来后,女人们纷纷露出了各色各样的腿,各种美腿都有各种丝袜装扮。白晓洁还是喜欢黑色丝袜,尽管腿粗,还是穿上了黑丝,外面套了条热裤,上身穿了件宽松的有蕾丝花边的黑衬衫。她的这身打扮,显得性感大方,还有种神秘感,一路上引来了许多男人的目光。
她奇怪地想,花荣要是看到这身打扮,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白晓洁在此之前,穿着十分随便,甚至有些邋遢,这些日子经常和花荣在一起,就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了,而且人也勤快多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知道,花荣不喜欢邋遢的女人。
每天上班前,穿好衣服,站在镜子前审视一番,才出门。
她感觉自己是穿给花荣看的,尽管他不在身边,其他人有什么看法都不重要,她也不会在乎。
到了公司,同事们都笑着看她。
她问一个同事:“笑什么呢?”
同事说:“哇塞,都认不出来了,真漂亮。”
白晓洁的脸红了,说:“什么呀,什么呀。”
同事说:“真的漂亮,没有想到丑小鸭也可以变成黑天鹅,呵呵。”
白晓洁说:“讨厌,嘲笑我。”
同事笑着说:“没有,没有,别往心里去。”
白晓洁也笑了:“呵呵,我可没有那么小心眼。”
那是个大热天,毒日头当空,往人间吐着烈焰。马路边悬铃木的叶子被阳光炙烤得蔫蔫巴巴,无精打采。走出汽车修理店,花荣睁不开眼,热气烘得他浑身臭汗。要不是车子出了点问题,需要修理,他才不会出门。此时,要是在家里开着空调,躺在床上看电视,那该有多么惬意。
他准备乘地铁回家。
从汽车修理店到地铁站,需要穿过两条街道。
马路两边的悬铃木挡住了阳光,走在人行道上,感受着树木的好处,最起码遮挡住了阳光。
树也是有灵魂的,花荣觉得每棵树上都有一双眼睛,在凝望着过往的人。
偶尔,他会站下来,和一棵树对视,花荣会意一笑,树便摇曳起来,仿佛起舞。花荣伸出手,摸摸树干,感受着树的体温,他和树便有了交集。
这个世界,没有人和他会有真正的交集,所以,他会和树亲近。
从小就这样。
花荣走到地铁站,在入口处看到了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样子。
那孩子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短裤,上身赤裸,瘦弱的身体,一根根肋骨从脏污的皮中突出,蓬头垢面,一双大眼可怜兮兮地看着过往的人。他的双脚畸形,像是断过骨头没有接好的样子。
孩子的旁边坐着一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衣衫脏污的瘦弱中年汉子,看上去满脸无奈和悲伤,他的眼睛血红。
他们的面前放着一个脏兮兮的铝盆,还有一块同样脏兮兮的白布,白布上写着:我儿残疾,本人又身患癌症,已经晚期,请好心人帮帮我们。
孩子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悯。
不时有人停下来,往铝盆里扔下些小面值的钞票和硬币。
花荣站在他们面前,看着孩子的眼睛,心里突然像被刀割,异常疼痛。他从兜里掏出钱包,拿了十元钱,弯下腰,将钱放进了铝盆。他直起腰时,目光和中年汉子的目光碰撞在一起,中年汉子的目光躲闪了一下,然后说:“谢谢,谢谢您。”
花荣没有说话,走进了地铁站。
这个时候不是上下班时间,地铁车厢里比较空,花荣很容易就找到了座位。他看到一个男子有空位也不坐,站在那里用贼溜溜的目光审视着车厢里的人。花荣心里不舒服,因为地铁口的那个孩子和父亲。
花荣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那个混蛋杀猪佬尽管让他吃尽了苦头,还是辛辛苦苦地赚钱供他上学。花荣考上大学时,杀猪佬十分吃惊,根本就不相信喜欢剥兔子皮的儿子会有如此造化,他拿着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跑到小镇的中学去问校长,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生怕是花荣做假骗他。得知花荣千真万确考上大学后,杀猪佬扬眉吐气,在小镇上四处张扬,生怕没有人知道此事。完事,他跑进小镇的一家小酒馆喝得烂醉,回家时倒在了路边,狂吐。一只胆大的老鼠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吃他吐出的秽物,他对老鼠说:“兄弟,你告诉你的朋友们,我儿子考上大学了。”花荣把父亲弄回家,放在天井里。花荣关紧家门,把父亲的衣服剥光,然后把一桶桶冷水浇在他头上和身上。杀猪佬清醒过来时,发现儿子拿着一把剔骨尖刀,站在自己跟前。杀猪佬想起了那些被剥皮的兔子,一骨碌从天井里爬起来,惊恐地说:“儿子,我是你爹,不是兔子。”花荣冷冷地说:“老淫虫,你不是兔子,你怎么是兔子。”杀猪佬往后退缩:“儿子,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花荣说:“你说我要干什么?”杀猪佬说:“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不知道——”花荣哈哈大笑,然后说:“老淫虫,你也有今天。”杀猪佬说:“儿子,我知道以前对不住你,可是,可是我还是把你抚养成人了,现在你考上大学,有出息了,我真的替你高兴哪。”花荣逼近他,用剔骨尖刀指着他的鼻尖说:“你高兴的是我终于要离开你了吧,你可以把那个臭**找回来了吧。”杀猪佬无路可退,靠在墙壁上,浑身颤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花荣收回了刀,说:“吓坏了吧,我不会杀你,我怎么能杀你呢,你是我爹呀,对不对!留着你还有用,我上大学还要花钱呢,你还得给我供着,你欠我的,还没有还清,你还得继续杀猪,等我大学毕业后,你才能死,明白吗?”杀猪佬说:“明白,明白,我供你上完大学,做牛做马我也乐意,谁让你考上大学了,我们家的祖坟冒青烟了哇。”花荣一阵冷笑。
杀猪佬果然供他上完了大学才死。他不是死于花荣的刀下,也不是死于疾病,更不是终老而死,而是死于醉酒。在花荣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的某天,他一个人在镇上的小酒馆里喝了两斤白酒,醉得烂泥一般,小酒馆的人把他送回了家。几天后,他的邻居闻到了浓郁的臭味,撞开他的家门,才发现他死了好几天了,尸体都腐烂了。
花荣回到小镇时,宗族里的人已经把杀猪佬埋葬了。花荣没有去坟上祭拜父亲,而是张罗着卖房卖地。把房子和地卖了后,他去找那个当初偷柚子时放他一马的那个小姑娘。她爷爷早就过世了,她也长大嫁人了。花荣在离小镇很远的一个山村里找到了已为人妇的姑娘,给了她一万块钱,然后离开了。他本来想娶了那姑娘,带着她到城市里去的,没有想到她嫁了人。
花荣想起父亲,也不知道他的坟在清明时分有没有人去扫墓,也许已经变成了野坟了,长满了蒿草。
他内心还是十分酸涩。
本来在车厢里站着的那个眼光贼溜溜的男子走到一个少妇跟前,在她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少妇抱着一个孩子,红色的提包放在旁边。男子把手伸进了提包里,从里面拿出钱包,迅速地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他若无其事地站起来,朝列车门边走去。经过花荣旁边时,花荣伸出了腿,绊了他一下,男子一个趔趄,摔倒下去,花荣扑过去,按住他的头,膝盖顶在他的腰上,说:“把钱包拿出来!”男子说:“放开我,放开我——”花荣说:“把钱包拿出来。”男子说:“抢劫啦,抢劫了——”花荣从他口袋里掏出了那个钱包,对不明真相的人们说:“这是个贼。”车厢里的人冷漠地看着他。他站起来,走到少妇面前,把钱包还给她,说:“以后小心点,这年头贼多。”少妇连声说:“谢谢,谢谢。”到站车门打开后,那男子蹿出门,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
白晓洁走进卫生间。
刚刚坐在马桶上,就听到旁边有两个女人在说话。她听出来了,是杨红和新上任的市场部总监赵露在说话,她们真是臭味相投,连上厕所也约好了一起上。白晓洁听明白了,她们竟然在说她。她们仿佛是故意说给她听的,明知有人进卫生间,还毫不顾忌。
杨红说:“那个小妖精真不知天高地厚,看她穿得那骚样,不晓得想勾引谁,看她老在老板的办公室门口晃来晃去。”
赵露说:“我看她也不顺眼,什么本事也没有,还挺傲气的,交代她做事情,连个笑脸都没有,朱燕不知道看上她什么,把她招进公司。现在朱燕走了,她没有靠山了,当然想找个靠山啦,可是,我们老板是什么人,能看得上她这样的货色。”
杨红笑出了声:“就是,我看公司里再猥琐的男人也不会瞧上她,她得瑟什么呀。”
赵露说:“等我工作理顺了,找个机会开掉她。”
杨红说:“先别急,我们不能开她。”
赵露说:“为什么?”
杨红说:“我们开她太便宜她了,还要给她补偿,要想办法让她自己辞职,那样,她就什么也拿不到了。”
赵露说:“有道理,有道理,还是你厉害。”
杨红说:“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
赵露说:“没有呀,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杨红说:“我想去清碧山庄泡温泉,你有兴趣吧。”
赵露说:“好呀,好呀,这段时间太累了,是要出去放松放松。”
杨红说:“就我们俩,不许带你老公哟。”
赵露说:“放心吧,就我们俩。”
“……”
白晓洁听着她们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愤怒极了。要不是因为父亲重病在身,她肯定会马上辞职,和这些**都不如的人在一起工作,是侮辱自己的人格和智商。
花荣没有回家,钻进了一家洗脚店。洗脚店里的空调开得很冷,让他十分舒服,他大口地吸着冷气,仿佛要把五脏六腑也冰凉。找了个姑娘按脚,他躺在沙发上,对姑娘说:“好好给我按,不要和我说话。”
姑娘笑了笑说:“放心,你睡一觉吧,我不说话。”
花荣感觉这是个乖巧善良的姑娘。
他相信自己的感觉。
每次看到乖巧善良的姑娘,他第一个念头就想娶她回家做老婆,可很快地否定这个古怪想法,还是一个人过吧,一个人安全,无牵无挂,他早就习惯了孤独,习惯了一个人抵抗岁月侵蚀。
花荣闭上了双眼。
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出现那地铁口行乞的父子。
想到孩子那双可怜巴巴的大眼,花荣十分紧张。
他手心捏着一把汗。
曾经,他的眼神也是那么痛苦无助,还有仇恨。花荣尽量回避童年往事,想起那些事情,他就会特别紧张,紧张到不能忍耐时,就会发狂,那时,他就要把自己泡到凉水之中,让自己渐渐地冷静下来。他很清楚,发狂是最伤自己的,而且无济于事,只有冷静,才有力量,才能掌控一切。
这也是他进洗脚店的原因。
洗脚店里的冷气和姑娘的按摩都有效地缓解他心里紧张的情绪。
渐渐地,花荣平静下来,孩子的眼睛也从脑海移除。
过了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
姑娘笑了笑,放下他的脚,站起来,去拿了个毛巾被,盖在他的身上。
姑娘给他按完脚了,他还在沉睡。
她微笑着走了出去,轻轻地关上了房间门。
花荣做了个梦。
梦见一个孩子躺在荒凉的原野上,不知道是死是活,他的眼睛紧闭,身体一动不动。冷风嗖嗖,孩子身边的野草沙沙作响,不停起伏。那是只野兔吗?是的,灰色的野兔。它从草丛里钻出来,机警地打量着躺着的孩子。许久,它发现孩子的确不会动了,或者沉睡,孩子死亡。灰色野兔才蹦跳过去。灰色野兔在孩子的头发上嗅了嗅,仿佛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就吃起了孩子的头发。是的,灰色野兔把孩子的头发当成青草了。它津津有味地吃光了孩子的头发,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还是一动不动。灰色野兔吃完孩子的头发,并没有离开,它又嗅了嗅孩子的头皮,又仿佛闻到了青草的味道,于是兔牙就在孩子的头皮上啃了起来。孩子的头皮被兔牙啃得鲜血淋漓……灰色野兔竟然把孩子给吃了,连同他的衣服,吃得干干净净,草地上只剩下血迹。
这是个奇怪的梦。
兔子竟然吃人。
花荣醒来,想起梦境中发生的事情,笑了笑。
这一觉也睡得太久了,走出洗脚店,已近黄昏。
夕阳西沉,天气还是热得难以忍受。花荣看了看表,心想,该去取车了。他没有乘地铁,而是打了辆出租车,前往汽车修理店。出租车司机是个50多岁的男子,看上去就是老车油子。花荣不想和他说话,他却主动挑起话题:“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花荣没好气地说:“我做什么工作关你鸟事。”他笑了笑:“是呀,关我什么鸟事,我这嘴就是贱,不说话会死。”花荣说:“你的脾气还不错。”他说:“那要看情况了,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花荣说:“什么时候?”他说:“交管理费的时候。”花荣说:“为什么这样说?”他说:“你以为我们开出租车容易呀,每个月交那么多管理费,还要扣这钱那钱,油价飞涨,车费不长,一个月辛辛苦苦下来,到自己腰包里的钱就所剩无几了。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好脾气。”花荣笑了:“你说得也对,换上我,也会有脾气的。”他说:“你说说,这出租车还是人开的吗?碰到操蛋的乘客,还嫌车费贵了,有的还诬陷你绕路,时不时投诉你一下,真他妈的窝火。”花荣说:“那你可以不干呀。”他说:“先生,你说得轻巧,我要不干,还能干什么,我都这把年纪的人了,况且,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呢。”花荣说:“实在不行,就开黑车吧,开黑车没有那么多烦恼。”他说:“我哪有钱买车呀,就是买了车,你以为就可以当黑车开,你听说过钓鱼吗?要被钓上了鱼,日子就不好过了,还是算了吧,老老实实开我的出租车,有一天过一天吧,只要饿不死就行了。”花荣不说话了。
到了目的地,花荣付完钱,正要下车,出租车司机说:“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
花荣说:“很重要吗?”
他说:“相当重要,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会难受一个晚上。”
花荣说:“不瞒你说,我是开黑车的。”
他睁大了眼睛:“啊——”
取了车,花荣就到附近的一家小面馆吃了碗肥肠面,然后就去张扬路幸福小区接小姐去夜总会上班。那几个浓妆艳抹的小姐挤满了他的车,车里散发着浓郁的香水味。花荣说:“你们以后少喷点香水好不好,我都被你们熏得喘不过气来了,我要走神了,出了车祸,你们可不要怪罪我啊。”
小姐们就七嘴八舌地数落他。
在她们的数落声中,花荣沉默。
他不喜欢和她们斗嘴,因为占不了便宜,这些女子久经沙场,什么人没有见过,什么话没有说过,花荣岂是她们的对手。
花荣觉得她们都是兔子。
每当有这样的感觉,花荣就会想到后备箱里的那把剔骨尖刀。
要不是她们人多,花荣就会把车开到那废置的别墅区里去。
那些兔子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危险。
送完她们,花荣把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喘着粗气。他的手很痒,颤抖着。花荣的牙咬得嘎嘎作响,眼睛里闪烁着冰冷的寒光,剔骨尖刀般的寒光。实在难以忍受,他脱下帽子,用自己的头去撞方向盘。
他满脑子都是兔子,都是剥兔子皮的场景。
此时,兔子在哪里,在哪里?
快下班时,赵露叫白晓洁到她办公室去。
白晓洁感觉到事情不妙,她们要对自己下手了?同事们用复杂的目光看着她走进赵露办公室,他们的目光里有同情,有忐忑不安,有猜测,有说不清的情绪……他们都担心自己被莫名其妙裁掉。赵露一上任,公司里就有流言传出,说要裁掉一些朱燕的人,第一个目标就是白晓洁。谁也不希望自己被赵露定为“朱燕的人”,有些人就开始暗中对赵露表忠心,撇清和朱燕的关系;也有些人不想待在这个公司了,开始找下家,一旦找到工作就跳槽;还有些人在观望……白晓洁走进赵露办公室,冷冷地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她本来想面带微笑,口气柔和说话的,可是她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很清楚,这样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问题是白晓洁根本就不会伪装,就像当初阿南死后,她毫无保留地坦白了和他的恋情。
赵露笑了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说:“晓洁,坐吧,别那么紧张。”
白晓洁坐下来,没有正眼看她,只是看着她身后墙上的一幅画。
画中一个变形的女人张着大嘴呐喊。
这应该是朱燕挂上去的画,她没有收走,赵露没有撤下来换上自己喜欢的画。
赵露说:“我也喜欢这幅画,所以就留着了。”
白晓洁没有说话。
赵露说:“晓洁,你对我有抵触情绪,这样不好,我们还要在一起工作呢。”
白晓洁真想缓和与她紧张的关系,说些好话,可是话一出口,就变了味:“不是我有抵触情绪,而是你们抵触我。”
赵露还是面带微笑,温和地说:“晓洁,你这话就有点过了,我可没有和你作对,我刚刚上任,还希望得到你的支持呢,没有大家的支持,我的工作怎么开展?我不会傻到放弃工作和你对抗吧,那样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
白晓洁想起她在卫生间里和杨红说的话,就特别恶心,她竟然还说这样冠冕堂皇的话,真是当了**还要立牌坊。白晓洁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赵露又说:“晓洁,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这不要紧,你还不了解我,以后时间长了,你自然会改变对我的看法的。我和你一样,都是打工的,我没有必要和任何一个人过意不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就对了,你说是不是?”
白晓洁还是不说话,低着头。
赵露说:“叫你来,还是工作上的事情。”
接着,她让白晓洁做一份新产品上市的策划案,而且要得很急,明天上班就要交给她。她把新产品的资料给了白晓洁。
白晓洁手中拿着那厚厚的一沓资料,说:“这不应该是我的工作,我是负责市场调查的。”
赵露笑着说:“我知道,我想在工作上做些调整,以后你就不要管市场调查这块了,今天晚上辛苦你,把这个策划案写出来吧,的确很急。”
白晓洁说:“这——”
赵露说:“晓洁,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这点事情难不了你。就这样,快去做事情吧,加个班,加班费我会考虑的,我不会让我手下吃亏的。对了,你写完,把策划案发我邮箱就可以了,明天上午你在家休息吧。”
白晓洁真想把那沓资料甩在她的脸上,然后提出辞职。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忍辱负重地走出了赵露办公室。
赵露看着她的背影,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到了下班时间,赵露和杨红有说有笑地走了,同事们也陆陆续续地走了,最后,只剩下白晓洁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加班。
白晓洁自言自语道:“要把我赶走,没有那么容易。”
她咬了咬牙,静下心来干活。
一直到凌晨三点,白晓洁才把写完的策划案发到赵露的邮箱。
发完邮件,白晓洁感觉自己要虚脱了,又累又饿。想到自己的境遇,白晓洁又委屈又伤感,心里特别难过。在这孤独的夜里,谁是她的依靠?
她突然想到了花荣,于是决定给他打个电话。
花荣说:“我刚刚送那几个小姐回家,你现在在哪里?”
白晓洁听到花荣的声音,就想哭。
花荣说:“晓洁,说话呀,你怎么了?”
白晓洁说:“我,我想你——”
花荣说:“你在哪里?在家吗?我马上过来。”
白晓洁说:“大哥,我在公司,你赶快过来吧,我快崩溃了。”
花荣说:“晓洁,你别急呀,我马上过来,等着我。”
花荣感觉到自己的额头鼓起了包,疼痛。他这才停止了撞头,内心也安稳了些。花荣扭过头,发现车窗玻璃上贴着一张脏污丑陋的脸,一双空洞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花荣惊叫了一声,赶紧戴上了帽子。
车外的人见他紧张,也吓了一跳,竟然撒腿就跑。
花荣看清楚了,这是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花荣开动了车,追了上去。流浪汉没命地奔跑,花荣叹了口气,停车,看着流浪汉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中。也许这个流浪汉是这些年来唯一看到花荣的头没有被他杀死的人。
在内心,花荣已经杀死了他。
花荣突然想到了地铁口的那个孩子。
他和他父亲是不是还在那里要钱?
花荣开着车来到了那个地铁口。
孩子的父亲刚刚准备走。他把孩子背在背上,朝一条偏僻的小街走去。花荣开着车缓缓地跟在他们后面。他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只是跟着他们。
在这个街区,有栋十三层楼的楼房是无人居住的,也没有被拆掉。这栋楼房是这个城市的阴影。传说,这栋楼房是这个城市最早的商品房之一,楼房建成后,陆陆续续有人搬进去住,后来,住进去的人又陆陆续续搬走了,不到两年,变成了一栋空楼。据说,经常到了深夜,有个女人会从十三楼一直哭到一楼,又从一楼哭到十三楼,如此反复,直到天亮。某住户听到哭声,开门想看个究竟,的确可以看到一个女人,身上穿着红色旗袍,脚蹬红色高跟皮鞋,梳着飞机头,发髻上插着朵玫瑰花。女人的脸煞白,嘴唇上涂着口红。她会朝开门的住户笑笑,扬了扬手中的丝绸手帕,朝楼上飘去。她的两脚不着地,飘得十分缓慢。住户见她消失在楼梯拐弯处时,又响起了凄婉的哭声。那住户吓得魂飞魄散。可不止一个住户发现这个穿旗袍的女人。有人深夜回家,刚刚到电梯门口,没按电梯的按键,电梯门就自动开了,进入电梯,电梯门关上后,竟然发现穿旗袍的女人背对着他在哭泣,等他出了电梯门,回头一看,电梯里什么也没有了。还有人晚上起来上厕所,进入卫生间,一开灯就发现马桶上坐着个穿旗袍的女人……关于空楼的传说很多,花荣从某份报纸上得知,空楼所在地原来是个妓院。
孩子父亲背着他,穿过那条偏僻的小街,就来到了空楼前。
他背着孩子走进了空楼。
空楼一片漆黑,鬼气森森。
花荣停好车,下车,站在空楼前的空地上,心想,他们难道是这里的住户?
他抬起头,一个个窗口搜寻着,看哪个窗口有灯火,却什么光亮都看不见。空楼早已经停水停电,哪来的灯光。花荣从车上拿出手电,从刚才那父子俩进入的门洞走进去。楼里静得可怕,花荣是个胆大包天的人,可在上楼梯时,还是心里发冷,尽管身上流着汗。走到四楼时,他听到了有人吼叫的声音,接着传来女人的哭声,还有孩子的哭声。
他迟疑了一下,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强烈的好奇心让他留了下来。
那些声音大约是从六七楼中传出的。
花荣一步一步沿着楼梯走上去。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些声音果然是从六楼左边的单元房里传出。花荣蹑手蹑脚地走到单元房门口。伸出手,轻轻推了一下门,门竟然开了条缝,暗淡的光从门缝漏出。花荣的目光从门缝穿过去,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房间里什么家具都没有,却凌乱不堪,地上铺着席子,孩子坐在席子上哭。是一根蜡烛照亮了他们灰暗的脸,以及房里的空间。中年男子手指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怒骂着。女人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男子似乎火很大,花荣听了会儿,就知道他火大的来由了。原来,他回来后,准备吃饭,发现女人忘了给他买酒,他就朝女人大发脾气。男子越来越凶,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根本就不像癌症病人。
女人哭着哀求:“虎子他爹,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现在就去买,行不?”
虎子爹突然伸手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到墙边,使劲地将她的头往墙上撞。
女人哭嚎着:“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我早就不想活了,跟着你这个王八蛋,我吃尽了苦头——”
虎子喊叫道:“爹,爹,别打妈妈了,爹——”
他朝父母亲爬了过去。
爬到父亲跟前,他抱住了父亲的脚,哀求道:“爹,放开妈妈,放开妈妈——”
虎子爹依然把老婆的头往墙上撞。
虎子突然张口朝父亲的小腿狠狠地咬了下去。
虎子爹惨叫一声,一脚踢开了虎子,抓住老婆的手终于松开了。虎子爹的目标转移到虎子身上,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吼叫道:“小王八蛋,竟敢咬老子,看我不踢死你。”说着,他飞起一脚,朝趴在地上的虎子踢去。
女人扑上来,抱住了他,喊叫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把孩子害成这样,还要踢他,你是畜生,畜生——”
花荣想到了母亲,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想到了那个杀猪佬……花荣浑身发抖,急促地喘息。他还想起了下午在洗脚店做的梦,虎子爹就是那只吃人的兔子,他该死,该死!
他实在按捺不住了,一脚踢开门,冲了进去,朝虎子爹怒吼道:“你他妈的给我住手!”
虎子爹惊愕地望着他,怔在那里。
虎子妈也松开了抱住丈夫的手,愣愣地看着他。
虎子还在哭,边哭边说:“叔叔,救救我妈——”
花荣突然把虎子爹扑倒在地,抡起拳头,朝虎子爹头上猛击。
虎子爹哀嚎着,无力还手。
虎子妈朝花荣跪下,说:“好人,你放了他吧,他要真死了,我们娘俩该怎么办。”
花荣仿佛看见自己的母亲在求饶,在母亲面前,他从来都是个乖孩子。他停住了手,从虎子爹的身体上翻下来,坐在脏乎乎的席子上,喘着粗气。虎子妈过去,用毛巾擦着虎子爹头脸上的汗水。虎子爹推开了她,坐起来,血红的眼睛里冒着仇恨之火。
虎子妈不理他了,坐在虎子的身边,把虎子搂在怀里,说:“虎子,痛吗?”
虎子说:“妈妈,我不痛,你痛吗?”
虎子妈说:“妈妈也不痛,妈妈习惯了,早就不知道痛了。”
花荣颤抖着手,从兜里摸出一包烟。
他点燃了香烟,狠狠地吸了口,然后吐出浓浓的烟雾。
花荣说:“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虎子妈的泪水又涌出了眼眶。
花荣说:“别哭,好好说,看我能不能帮助你们。”
虎子妈开始了哭诉。
虎子妈的哭诉,让花荣颤抖,仿佛自己和母亲在经受非人的折磨。
他知道了残酷的真相:虎子爹在虎子没有出生时,就外出打工,虽然辛苦,一年也有些积蓄,比在家里种田强。虎子降生后,虎子爹高兴,在外面省吃俭用,每个月都有钱寄回家。虎子的姥姥常说,虎子妈跟虎子爹是跟对人了。就在虎子五岁那年的夏天,虎子爹突然不寄钱回家了。一连三个月,虎子爹不但不寄钱,连电话也不往家里打一个。虎子妈急了,不寄钱不要紧,是不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虎子妈就带着虎子来到了他打工的那个城市。通过同样在这个城市打工的老乡,虎子妈找到了他。他住在郊区的一栋烂尾楼里。老乡叫他时,他还冲出烂尾楼,没命地跑。发现是老乡带着妻儿,才停住脚步,回过头,呵斥妻子:“你来做什么?”老乡见状,对虎子妈说:“我帮你找到他了,没我的事情了,我先走了。”老乡走后,虎子妈看着蓬头垢面的他,说:“你跑什么?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虎子爹也不说什么原因,而是责备她带儿子来找他。
那天晚上,她带着虎子住在四面透风的烂尾楼。虎子睡着后,她对丈夫说:“你到底怎么了?也不去做工,也不回家,躲在这个破地方干什么?”虎子爹沉默不语。她说:“不管怎么样,明天和我们一起回家吧,家里有田有地,饿不死我们的。”良久,虎子爹才说:“我不回去,不回去!”她说:“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虎子爹说:“我欠了一屁股赌债,没脸回去呀,回去了又怎么样,他们还是可以找到我的。”原来他被一个同乡拉下了水,赌上了瘾,非但不给家里寄钱,还欠下了繁重的赌债。虎子妈哭了:“这可如何是好哇——”他又沉默了。天一亮,他对妻子说:“我们逃吧。”虎子妈说:“逃哪里?”他说:“随便,只要逃出这个城市就可以,到哪里都成。”虎子妈无奈,只好同意。于是,他带着妻儿,来到了这个城市。刚到这个城市时,他发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在一个菜市场里找了个工作,帮人家搬运蔬菜,虽然钱不多,也够他们吃喝。可是不久,他又故态复萌,每天晚上和菜市场的一帮下三滥去赌博,辛苦赚来的钱不够输的。
那时,刚好虎子妈得了病,卧床不起,虎子饿得直叫唤。他也心痛老婆,没钱带她去看病,着急。有一天,他把儿子带出去了,很晚才回来。他高兴地对妻子说:“有钱了,有钱了,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病。”她说:“你哪里来的钱?”虎子这时哭起来,喊着:“妈妈,我痛,我痛——”虎子妈强忍着从床上爬起来,看到儿子的双脚断了,缠着破布。虎子妈明白了,他是把儿子的腿弄断,骗取人们的同情要钱哪!她疯了般朝丈夫扑过去,撕心裂肺地喊叫道:“畜生,畜生——”虎子爹把她甩到床上,恶狠狠地说:“臭婆娘,老子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
从那以后,虎子爹就经常把儿子的腿弄断,带着他出去要钱,久而久之,孩子的腿就真的残了,连路也不会走了。他们搬到了这栋空楼上,住在这里。每天晚上回来,虎子爹就要喝酒,没有酒喝就打骂妻子。
虎子妈哽咽地说:“大哥,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后悔,后悔嫁给了这个畜生,后悔带孩子出来找他,现在,我们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可怜的虎子,他的一生就这样给这个畜生毁了。”
她不停地流泪。
虎子说:“妈,别哭。等我们赚了很多钱,就回家,回姥姥家。”
她抱紧虎子,说:“嗯,嗯。”
她心里清楚,那些钱不够虎子爹喝酒的,猴年马月才能赚够钱回家。
虎子爹装死,躺在那里,闭着眼睛,还装着打起了呼噜。他是希望花荣这个不速之客早点滚蛋,然后接着收拾虎子妈。虎子妈把一切都告诉给了这个陌生人,让他丢了大脸。而此时,在花荣眼中,他是一只兔子了,一只等待他剥皮的兔子。
花荣抱着她,轻轻地说:“别怕,我在呢。”
白晓洁安详睡去,他身上仿佛散发出一种让人迷醉的气味,这种气味还有催眠的功效。他在,白晓洁就有了安全感。
白晓洁睡了一个安稳觉。
她醒来时,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她不知道花荣是什么时候走的,想起他,心里有些幸福,有些甜蜜。
白晓洁希望这样的感觉能够长久下去。
她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黑车司机。
也爱上了他那些杀人故事。
白晓洁洗了个澡,梳妆打扮,收拾利索后,就去公司上班。
刚刚在办公桌前坐下,旁边的同事就对她说:“赵露让你来了后就到她办公室去。”
白晓洁想,是不是自己的策划案写得太好了,她对自己改变了看法,要表扬自己呀。
不过,她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
白晓洁忐忑不安地走进赵露办公室。
赵露在打电话,见她进来,朝她打了个让坐的手势。
白晓洁坐了下来,目光落在她身后墙壁上的那幅画上。
赵露说:“好了,我们有空再聊吧,我现在有事了。”
她挂了电话,朝白晓洁笑了笑:“休息好了?”
白晓洁说:“休息好了。”
赵露说:“那就好,辛苦你了,昨晚一定很晚才回家吧。”
白晓洁说:“凌晨四点多才回家。”
赵露说:“你的敬业精神真让我感动。”
白晓洁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赵露说:“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想,那该有多好。”
扯了那么多废话,还没有说到正题,白晓洁有点急了,说:“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赵露脸上还是堆满笑容:“还是那策划案的事情。”
白晓洁说:“出什么问题了?”
赵露说:“凭良心说,你的策划案写得不错,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真的不容易。可是,我交给老板审阅后,他认为还不够好,提出了几点意见,要我们完善。”
白晓洁心里明白了什么。
她突然对赵露脸上假惺惺的笑容十分厌恶。
赵露接着说:“你还是拿回去好好改改吧。意见都写在打印稿上了,你琢磨琢磨,看怎么完善。”
说着,她把一个文件夹递给白晓洁。
本来,打回来让白晓洁修改,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她感觉这里没有那么简单,赵露是在给她施加压力,目的就是要让她受不了,让她自己提出辞职。
这时,电话铃响了。
赵露拿起了电话,说:“我是赵露——喔,杨红呀——没有变化,明天早上出发——你来接我也可以,会不会麻烦呀——好吧,好吧,明天见,是该好好泡泡温泉,松松骨了,这段时间累坏了——什么?这事呀,现在不方便说,明天见面再谈吧,好,明天早上我在家等你,放心吧,我很利索的,你车一到,我们就出发。拜——”
对了,明天是周末了,白晓洁知道她们要去郊县的清碧山庄泡温泉,她们过的才是生活,什么时候白晓洁能够像她们一样,白晓洁不得而知。
赵露对她说:“你去忙吧,最好晚上加个班,明天早上发我邮箱。”
白晓洁说:“明天不是周末吗?”
赵露说:“是周末呀,这不影响我工作呀,老板那里催得很急,我也没有办法,辛苦你了,晓洁,放心吧,我不会亏待你的。”
白晓洁心里骂了声:妈的!说得比唱的好听,你不就是要赶我走吗?直说呀,用这样的手段整我,以为我是白痴呀!靠!什么东西。
花荣站起来,用脚尖撩了撩躺在席子上装睡的虎子爹,说:“起来吧,我请你喝酒,你不是想要喝酒吗?”虎子爹一听到酒,睁开血红的眼,从席子上弹起来,说:“你说话算数?”花荣冷笑了一声说:“你看我像说话不算数的人吗?”虎子爹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我看你是个实在人,下午你给我们十块钱,我还记得呢。”花荣说:“记得就好,走吧。”虎子爹说:“可是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花荣说:“我是谁很重要吗?”虎子爹说:“不重要,不重要,喝酒比什么都重要。”
花荣对虎子妈说:“你们赶快吃饭吧,我和他去喝酒。”
虎子妈说:“好人,不要让他喝多呀,他是个畜生,没有酒喝打人,喝多了,也打人,我们娘俩都受不了他了。”
花荣说:“你们放心吧,晚上睡个踏实觉吧,他再也不会打你们了。”
虎子妈和虎子茫然地看着他。
花荣弯下腰,摸了一下孩子的头,说:“虎子,好好陪着妈妈。”
虎子点了点头。
虎子爹说:“大兄弟,走吧,酒瘾上来难受哇。”
花荣对他说:“走吧。”
花荣和他走出门。虎子爹关上门,把微弱的烛光关在了里面。楼道里一片漆黑,就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夜,也阴气逼人,花荣虽然胆大,但在这鬼楼里,也觉得瘆人。他打亮了手电。虎子爹说:“我摸黑都可以下楼,习惯了。”花荣说:“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虎子爹说:“有好几个月了吧。住这里好哇,没有人会来赶我们,我就纳闷了,这么好的房子怎么就没有人住呢?”花荣没有说话。
从四楼下到三楼,走下最后一阶楼梯时,花荣手中的手电突然不亮了,一脚踩空,趔趄着差点倒在地上。虎子爹扶住了他,连忙说:“大兄弟,你没事吧?”花荣说:“没事,没事。”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电梯门开启的声音。
这楼都停水停电了,怎么电梯门会打开?
紧接着,他们听到女人嘤嘤的哭声。
花荣打开手电开关,手电竟然亮了。手电光朝电梯门照射过去,花荣看到电梯里站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她双手下垂,低着头,看不到她的脸,只能看到她的发髻,发髻上插着一朵玫瑰花。
花荣大惊失色。
虎子爹朝电梯里的女人大喝道:“他娘的,不好好待着,又出来吓人了,滚开。”
电梯门哐当一声关闭了。
哭声也消失了。
花荣说:“还他妈的真有鬼。”
虎子爹说:“她每天晚上都出来,我们都习惯了,不怕了。”
花荣身上汗毛倒竖。
花荣快步下楼,走出空楼,他的心才安定下来。
虎子爹笑话他,说:“大兄弟,你胆子好小呀,活人岂能怕死鬼。你们城里人就是胆小,你去问问虎子和虎子他妈怕不怕,他们会告诉你,这有什么好怕的。”
花荣冷冷地说:“他们就怕你,对吗?”
虎子爹说:“是嘞,他们都怕我。”
花荣说:“你也会怕我的。”
虎子爹说:“我怕你做什么?”
花荣说:“到时你就知道了。”
虎子爹说:“大兄弟,你的话真多,赶快找地方喝酒吧。”
他们随便找了个小酒馆,坐了下来。花荣说:“你喜欢吃什么?”虎子爹睁着血红的眼睛,露出一口黑乎乎的烂牙,说:“有酒就成,菜要不要都无所谓。”花荣冷笑了声,说:“这是你的最后一顿饭,要让你吃好点,不能随便。”虎子爹呵呵一笑,说:“大兄弟,你真会开玩笑。”
花荣点了一只白斩鸡,一条红烧鱼,一盘回锅肉,一个老鸭汤,外加一瓶洋河大曲。
他笑着说:“虎子爹,鸡鸭鱼肉都有了,满意吧。”
虎子爹说:“满意,满意。让你破费,真不好意思。”
花荣说:“满意就好。”
菜很快上桌,花荣给他斟上酒,说:“喝吧。”
虎子爹说:“你怎么不喝?”
花荣说:“我不喜欢喝酒,可是我喜欢看别人喝酒。”
虎子爹说:“你这人真怪。”
花荣说:“吃吧,喝吧,我看着高兴。”
虎子爹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虎子爹大杯喝酒,大口吃肉,像个饿死鬼。花荣注视着他,就像看着一只待宰的兔子。花荣说:“你不心疼你儿子?”虎子爹抬起头,嘴巴周边全是油腻,还有肉屑,他说:“你说什么?”花荣说:“你不心疼你儿子?”虎子爹往嘴里灌了口酒,说:“心疼。”花荣说:“心疼你还把他弄残。”虎子爹说:“没有办法,总得活人。”花荣说:“为了活人,你就可以让他一辈子受苦?”虎子爹说:“你没到那个地步,到了那个地步,你就理解我了。”花荣说:“你真是畜生,你老婆说得没错。”他怪异地笑了:“畜生也得吃饭。”
喝完一瓶酒,虎子爹觉得还不过瘾,花荣又给他要了一瓶。
喝完第二瓶酒后,虎子爹醉翻了。
这畜生喝醉后倒是老实,不闹腾。
花荣把他弄上车。
银灰色的现代轿车朝郊外驰去。
虎子爹躺在后排座上,哼哼着什么。
花荣将车开进了废置的别墅区,停车,没有马上熄火,而是坐在车上,点燃了一根烟。烟头一明一灭,他阴冷的脸也一明一灭。抽完一根烟,他说了声:“狗东西,喝那么醉,不能陪老子捉迷藏了。”
他下了车,伸了个懒腰,打开了后面的车门。
花荣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虎子爹拖下了车。
天很黑,看不清虎子爹的脸。
花荣找了些破木板,点了一堆火。
火渐渐地烧旺,照亮了周边坟墓般的别墅。
花荣把虎子爹拖到火堆旁边,剥光了他的衣服。在火的炙烤下,花荣浑身冒出了汗水,他脱掉了衣裤,只穿着一条短裤。虎子爹也被火炙烤得口干舌燥,不停地哼哼着,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
花荣从车上拿出扳手。
他走到虎子爹的跟前,蹲了下来,双眼充满了杀气。
花荣四处张望,这个地方除了他们俩,什么人也没有,要有,也是那些鬼魂。花荣现在什么也不怕。他举起扳手,狠狠地朝虎子爹的左膝盖砸了下去。虎子爹的脚本能地抖动了一下,他喝得太醉了,竟然没有反应。
花荣又举起扳手,狠狠地朝他的膝盖砸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花荣听到虎子爹膝盖骨碎裂的声音,心中充满了快感。虎子爹终于痛苦地叫唤起来:“痛,痛,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花荣冷笑道:“娘的,老子还以为你不知道痛了,你知道痛就好。”
接着,他举起扳手在他的右膝盖上狂砸。
虎子爹右膝盖骨被花荣砸碎后,他才从酒醉中清醒过来。
虎子爹撕心裂肺地叫唤着,睁着血红的双眼,双手抱着被砸断的腿。
花荣说:“叫吧,使劲叫吧。”
虎子爹痛苦叫唤时,花荣点燃一根烟,蹲在他面前,朝他脸上吐着烟雾。花荣说:“你现在知道痛了?”
虎子爹说:“痛,痛死我了。”
花荣说:“你儿子当初被你弄断腿时痛吗?”
虎子爹说:“痛,他也喊痛。啊,啊,痛死我啦——”
花荣说:“那你怎么忍心下那狠手?”
虎子爹说:“我,我没办法哇——”
花荣说:“你有办法的,只是你心黑透了,已经不是人心了,就像我的心一样,也黑透了,早已不是人心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会放过你,我说过,那是你最后一顿饭了,你还不信,还以为我是和你开玩笑的。”
虎子爹急促地说:“大兄弟,放过我,放过我,虎子他们没有我,不成。”
花荣说:“晚了。况且,虎子和他妈没有你,他们会活得更好,你要是活着,迟早要害死他们。”
虎子爹说:“不,不——”
花荣把烟头扔到火堆里,右手操起了扳手,狠狠地朝虎子爹右肘关节砸去。虎子爹躲闪不及,右肘关节被砸碎了。接着,花荣又把他的左手关节砸碎。虎子爹疼痛得直吐舌头,连叫都叫不出来了。
他血红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死亡的恐惧。
花荣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说:“你不是连鬼都不怕吗?你不是胆大包天、心狠手辣吗?现在怕了吧?”
虎子爹颤抖着说:“怕,怕——”
花荣说:“怕什么?”
虎子爹绝望地说:“怕,怕你。”
花荣说:“还怕什么?”
虎子爹说:“还,还怕死——”
花荣说:“我就是要你怕,要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当你知道自己要死,无力挽回自己生命时,是最恐惧的,对吗?”
虎子爹说:“对……对……大……大兄弟……放……放过……我……我吧……我……我还没有……活……活够——”
花荣说:“其实,你这样的人,活着和死了,都一样。”
说着,花荣抡起扳手,朝他的脑袋上狠狠地砸下去。
……
花荣搂着白晓洁,给她讲完杀死虎子爹的故事,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
花荣说:“怕不怕?”
白晓洁装着害怕的样子,往他怀里钻,笑着说:“怕,怕,怕死了。”
花荣也笑着说:“你就装吧,有你真正害怕的那天。”
白晓洁说:“你还没有讲后来虎子妈和虎子怎么样了。”
花荣说:“后来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取出来,准备给他们,让他们回老家过安稳日子。可是,我去空楼找他们时,他们却不见了。找遍了整个楼的所有单元房的所有房间,都没有找到他们。一连好几天,我都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上寻找他们,可是没有他们的踪影。”
白晓洁说:“他们会不会被那个女鬼带走了?”
花荣说:“不清楚。”
白晓洁说:“他们真可怜。”
花荣说:“你也很可怜。”
白晓洁说:“为什么?”
花荣说:“和一个杀人犯在一起,你竟然不害怕。”
白晓洁说:“胡说,你是天下最好的男人。我喜欢你给我讲杀人的故事,好刺激的,不过,今天晚上讲的故事有些伤感。”
花荣说:“是因为虎子和他妈?”
白晓洁说:“是的。”
花荣搂紧她,说:“你真是个善良的傻姑娘。”
突然,白晓洁闻到了那神秘的香水味。她抽动着鼻子,警觉的样子。花荣说:“晓洁,你怎么了?”白晓洁说:“我闻到了香水味。”花荣也抽动了鼻子,然后说:“哪来的香水味呀,你这是幻觉吧。”白晓洁说:“我真的闻到了香水味,不骗你的,你的鼻子一定有问题。”花荣说:“好了,睡吧,不要疑神疑鬼了。”白晓洁说:“真的有股香水味。”花荣说:“好吧,有又怎么样呢?你害怕了?”白晓洁说:“你在我就不害怕,你要是不在,我就害怕。”花荣说:“天快亮了,我该走了。”
白晓洁紧紧地抱着他,说:“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
花荣说:“你还不是我老婆,等哪天你成为我老婆了,我就不会走了,会一直陪着你睡,明白吗?”
白晓洁说:“你真老土。”
花荣说:“随便你怎么说,我该走了。”文学度 www.wenxuedu.org
如果您中途有事离开,请按CTRL+D键保存当前页面至收藏夹,以便以后接着观看!